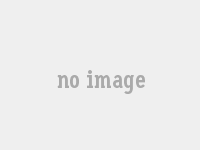概況
《文史通義》“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
《史通》問世之後,對于後世史論的發展,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因此,宋元期間,相繼産生了如鄭樵的《通志》、範祖禹的《唐鑒》和吳缜的《新唐書糾謬》等。繼宋元之後,明清兩代評史論史之風更盛,而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堪稱能與《史通》匹敵的第二部史學理論巨著。章氏在《文史通義》中,不僅批判了過去的文學和史學,也提出了編寫文史的主張。他對編纂史書的具體做法,又表現在他所修的諸種地方志之中。
章學誠為什麼撰寫《文史通義》呢?章學誠撰寫《文史通義》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闡發史意或史義。由于他對劉知幾、鄭樵、曾鞏等人的史學成就,不是全部肯定,而是吸收他們有益的東西。他在《和州志·志隅自叙》一文中說:“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
此予《文史通義》所為做也。”在這裡,他通過與以上諸家的比較,明确指出自己撰寫《文史通義》一書,就是為了闡發史意。此外,他還在《文史通義》的許多篇章中談到了闡發史意的重要性。例如他在《文史通義·言公》篇中說:“做史貴知其意,非同于掌故,僅求事文之末。”在《文史通義·史德》篇中說:“史所貴者義也。”在《中鄭》篇中說:“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等等。
《文史通義》命名來源。章學誠為何如此強調史意的重要性呢?他認為史學主要包括史事、史文、史義三個部分,其中史義是靈魂,因此最為重要。他在《文史通義·申鄭》篇中說:“孔子做《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據此,章學誠把自己的著作命名為《文史通義》,表明他希望通過對史書和史文的研究達到通曉史義的目的。
内容簡介
《文史通義》八卷,,清章學誠(1738-1801)撰。始撰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逝世前尚未全部完成。分内篇、外篇兩部分。内篇五卷,泛論文史而側重于史,外篇三卷。多論方志。此書為繼唐劉知己《史通》以來最著名的史學論著,提出“六經皆史”的著名觀點,在劉知己史學“三長”(才、學、識)論基礎上,又提出“空德”說。
分史書為“著述”與“記注”兩類,推重“著述”。提倡編著通史和纂修方志,突出方志的史學性質。也反映了章學誠的經學觀點。章氏曾學劉宗周、黃宗羲之學,繼承清初“經世緻用”的傳統。此書内篇卷一為《易教》《書教》《詩教》《經解》,卷二《原道》《原學》,卷五《答客問》《浙東學術》等篇多論及經術。
在《匡謬》篇肯定“盈天地間惟萬物”,《原道》篇以為“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強調“道”是事物的規律,提出“道寓于器”、“因器而顯”的命題。在《經解》上篇提出“六經皆史”、“六經皆器”說,認為“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于政教行事之實”。否認六經為傳統權威,提出“賢智學幹聖人,聖人學于百姓”,“集大成者乃周公而非孔子”(《原道》篇)。
主張考證史料和發揮義理相結合,把治經引向治史,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易教》篇),反對當時的學風,在《原學》下謂“學博者于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鴦于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殉之,不知博之何所取也”,又謂“言義理者似能思亦,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于道矣”,所以在《浙東學術》篇又提出“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反對空談性命,主張“必習于事而後可以言學(《原學》)。
《博約》篇下謂“言學術功力,必兼性情”。“令學者自認資之所近與力所能勉者,而施其功力”。反對偏于形式。固執門戶的傳統治學方法,與正統派不同。
在《原道》篇下匿于前者,章句訓诂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于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随時撰述,以究大道也”“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郁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學術與一時風尚不必求适合”(《感愚》),開學術思想擺脫經學傳統束縛的風尚,故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稱此書“實為乾嘉後思想解放之源泉”。
有道光十二年(1832)章華绂大梁刊本,為初刊本,又有《粵雅堂叢書》本,民國十年(1921)劉承幹嘉業堂刊《章氏遺書》本,内篇六卷,共九卷,又有《叢書集成初編》本,《四部備要》本,1956年古籍出版社标點本,1985年中華書局《文史通義校注》本等。
其一,"六經皆史"論。關于我國史學的源流,《文史通義》開卷便宣稱"《六經》皆史也"。又說:"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在《浙東學術》中,進一步闡述:"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謂義理矣。"
章氏提出"六經皆史"的命題,以為《六經》皆屬先王的政典,記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說明史之源起先于經,并且指明經術乃是三代之史而為後人所重視。雖然"六經皆史"不是章氏的創見,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經亦史"的見解,但是在乾嘉時期,針對"漢學"注重"舍今求古"的考據和"宋學"專尚"空談性天"的兩個極端,"六經皆史"提出學術必須"切合當時人事",在客觀上卻有着積極的意義。
這個命題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學"經世"的思想,不但将史學的産生上溯至《六經》之前,而且擴大了古史研究的範圍,對先秦史學史和史料學的研究作出了貢獻。對于"六經皆史"的論述,《文史通義》的《易教》《書教》《詩教》《禮教》《經解》《史釋》《浙東學術》等諸篇,均有涉及。
其二,有關曆史編纂學問題。這是該書的主要内容之一,散見于《史德》《說林》《書教》《答客問》《原道》《釋通》《古文十弊》諸篇中。章氏發展劉知幾的史學理論,于"才、學、識"之外,提出"史德"問題。他說:"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史德》)具備"義、事、文"方可稱為"史學"。
"義"指曆史觀點,"事"指曆史事實,"文"則是表達的文筆。在章氏看來,三者以"義"為主,而"事"與"文"不過是求"義"的根據和技巧而已。然後,"義"畢竟是史家主觀的東西,那麼,如何使主觀的"義"與客觀的"事"一緻呢?章氏認為,"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
這是說,史家治史要有尊重曆史真實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這裡的"天人之際",是指客觀的史實與主觀的史家而言,要求史家不以主觀的偏見代替客觀的史實。所以,章學誠所說"史德"的内容,實際上就是"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隻要按照這個要求去做,就"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史德》)這是"欲為良史"的基本條件。
在章氏看來,古來史書就其性質而言,基本可分為兩大類,即所謂"撰述"和"記注"(《書教》),或稱為"著述"與"比類"(《報黃大俞先生》),又稱之為"著述"與"纂輯"(《博約中》)。雖然稱謂不盡相同,而含義并無區别。前者指史家的"獨斷之學",即史學著作;後者屬文獻資料彙編,即史料纂輯。章學誠可說是我國古代史學史上,第一個嚴格區别史著與史料的史學家。
在體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以為通史具有"六便"。撰述《通志》這種專門的學者。對于紀事本末體,章學誠亦備加贊許,以為"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書教下》),兼有紀傳史和編年史所不具備的優點。
其三,把方志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我國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載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指當時的地方志。自宋元以來,纂修方志之風日盛,清初修志之風更加盛行。
但是,把方志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提出系統的理論主張,始自章學誠。章氏不但對方志的性質、内容、體例等問題有獨到的見解,而且将其主張貫徹于具體的編修方志的工作中。章氏的有關方志的論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義》和《章氏遺書》中。這是章氏對方志學的傑出貢獻。
關于方志的性質,曆來把它列入地理類。章學誠認為,方志"乃史體",與地理不同。而"地理之學,自有專門"(《跋湖北通志檢存稿》),二者不能混淆。從性質上劃分了方志與地理的區别。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認為,它既然屬曆史,專載一方,就不應隻重地區沿革,而輕一方文獻。
因此,在體例上,他主張方志立三書,即記載大事記和人物的"通志"、記載典章制度的"掌故"、記載文獻詩文的"文征",以及作為附錄的"叢談"。為了征集文獻資料,便于編修方志,章學誠還提出了各州縣建立志科的主張。
由于章學誠是封建社會末期史家,在《文史通義》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評論,但也擺脫不了宣揚綱常禮教之例,如他把謗君和怨悱的人說成"亂臣賊子"、"名教罪人"。對于曆代史學名著的評論,其觀點仍有值得商榷之處。
書中所論史實,也存在錯誤的地方,如全祖望是清初有民族思想的人,他的文集大量表揚明末清初抗清的忠臣義士,章學誠僅從《鲒埼亭集》中看到全氏所撰碑傳事有重複,即把全祖望表彰民族氣節的一片真心,看成是為自己的文集争體面。這些是我們在閱讀《文史通義》時,應加以注意的。
作者簡介
章學誠(1738-1801年),字實齋,号少岩,浙江會稽(今紹興市)人,是我國封建社會晚期一位傑出的史學評論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不僅批判了過去的文學和史學,也提出了編寫文史的主張。他對編纂史書的具體做法,又表現在他所修的諸種地方志之中。
章學誠在這部書中提出了“經世緻用”、“六經皆史”、“做史貴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論斷,建立了自己的史學理論體系;同時還在總結前人修志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志屬信史”、“三書”、“四體”、“方志辨體”和建議州縣“特立志科”等重要觀點,建立了方志理論體系,創立了方志學,從而奠定了章學誠在清代史學上的重要地位。
章學誠在《與族孫汝南論學書》一文中回憶他的童年時說:“仆尚為群兒,嬉戲左右,當時聞經史大義,已私心獨喜,決疑質問,間有出成人拟議外者。”這說明章學誠自幼對經學和史學理論就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并且所發的議論經常令大人吃驚,在這方面顯示出良好的資質。
章學誠十五六歲時,随父親到湖北應城,從館師學習舉子業。但他對此卻很厭煩,于是偷偷說服了妻子,将金銀首飾摘下,賣錢換來紙筆,雇來縣裡的小書吏,連夜抄錄春秋内外傳,以及東周、戰國時的子、史書,然後根據自己的意圖,把它們分析開後重新組合,編纂成紀、表、志、傳體裁的史書,共100多卷。
可是這些事情還沒來得及完成,他便因“館師所覺,呵責中廢”。可見他在青少年讀書時期,主要經曆也是用在曆史編纂學方面的。
他真正萌生撰寫一部史學理論著作的想法,是在他29歲的時候。章學誠曾說:“嘗以二十一家義例不純,體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約為科律,作為數篇,讨論筆削大旨。”(《與族孫汝南論學書》)
章學誠在太學志局的不幸遭遇,是促使他下決心着手撰寫《文史通義》的直接原因。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章學誠因“二三當事,猥以執筆見推”,進入太學志局,參與《國子監志》的編修工作。但他一旦進入志局,便感到處處受牽制,難以施展自己的才幹。尤其令他氣憤的是,志局監領嫉賢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權力,颠倒是非,排擠和打擊真才實學之士。數年之後,章學誠忍無可忍,于是憤然離開志局。
離開志局後不久,他給曾任順天鄉試考官、一向很關心和器重他的朱春浦先生寫了一封長信,陳述了自己離開志局的原因和今後的打算。他說:“學誠用是喟然謝去,非無所見而然也。昔李翺嘗慨唐三百年人文之盛,幾至三代兩漢,而史才曾無一人堪與範蔚宗、陳承祚抗行者,以為歎息。夫古人家法,沈約以前,存者什五,子顯以下,存者什三。唐史官分曹監領,一變馬班以來專門之業,人才不敵陳、範,固其勢也。
每慨劉子元不以世出之史才,曆景雲、開元之間,三朝為史,當時深知,如徐堅、吳兢輩,不為無人,而監修蕭至忠、宗楚客等,皆癡肥臃腫,坐嘯畫喏,彈壓于前,與之錐鑿方圓,抵龉不入,良可傷也。子元一官落拓,十年不遷,退撰《史通》。是以出都以來,頗事著述,斟酌藝林,作為《文史通義》,書雖未成,大旨已見。”
劉知幾,字子元,是唐朝著名的史學理論家,曾在史官中任事多年,後因忍受不了史官人浮于事、相互扯皮和嫉賢妒能的腐朽官僚體制,憤然離去,退撰《史通》,于是成為一代史學名著。章學誠在這裡通過叙述劉知幾在史館裡的遭遇,不僅暗示了自己離開志局的原因,同時也說明了自己開始撰寫《文史通義》的原因和動機。
關于《文史通義》一書的寫作年代,章學誠未曾明确說過,但還是可以通過他的一些行迹和言談推斷出來。
在上面給朱春浦的這封信中,章學誠還說道:“出都以來,作為《文史通義》。”這表明《文史通義》一書的動筆時間,應當在他出都後不久。根據他信中說明的情況,章學誠是在出都的次年寫的《文史通義》,那時已經距離他離開故鄉整整20年了。章學誠離開故鄉是1753年,則《文史通義》的動筆時間應當是1772年,章學誠時年35歲。
由于章一生貧窮,為了生計常常要四處奔波,使他不可能安穩坐下來從事學術研究,所以《文史通義》一書的寫作時斷時續,進展十分艱難和緩慢。學誠逝世前一年,因為積勞成疾,已經雙目失明,即使這樣,仍筆耕不辍。但天不假年,他早已列入計劃的《圓通》《春秋》等篇還未及動筆,便遺憾地死去。可見,《文史通義》一書的寫作,自章學誠35歲起,至他64歲逝世時止,共曆時29年。但嚴格說來,仍沒有寫完。
主要内容
自中西文明發生碰撞以來,百餘年的中國現代文化建設即無可避免地擔負起雙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脈絡,已成為我們理解并提升自身要義的借鏡,整理和傳承中國文明的傳統,更是我們實現并弘揚自身價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彙,乃是塑造現代中國之精神品格的必由進路。《文史通義》是清朝乾、嘉時代著名學者章學誠的著作。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零一)字實齊,浙江會稽(今紹興)人,是著名的史學家,曾經為和州永清縣和亳州編寫縣志和州志,又編寫《湖北通志》,著有《章氏遺書》,從中選出精要部分為《文史通義》,後附《校雠通義》。《文史通義》是一部開新學術風氣的著作,書中主張借古通今,所論涉及史學、文學、校雠學等多種領域,創見頗多。
作品目錄
卷一内篇一
卷二内篇二
卷三内篇三
卷四内篇四
卷五内篇五
卷六外篇一
卷七外篇二
卷八外篇三
作品目的
章學誠撰寫《文史通義》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闡發史意或史義。他在《和州志·志隅自叙》一文中說:“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為做也。”在這裡,他通過與以上諸家的比較,明确指出自己撰寫《文史通義》一書,就是為了闡發史意。此外,章學誠還在《文史通義》的許多篇章中談到了闡發史意的重要性。例如他在《文史通義·言公》篇中說:“做史貴知其意,非同于掌故,僅求事文之末。”在《文史通義·史德》篇中說:“史所貴者義也。”在《中鄭》篇中說:“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等等。
《文史通義》命名來源。章學誠為何如此強調史意的重要性呢?他認為史學主要包括史事、史文、史義三個部分,其中史義是靈魂,因此最為重要。他在《文史通義·申鄭》篇中說:“孔子做《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據此,章學誠把自己的著作命名為《文史通義》,表明他希望通過對史書和史文的研究達到通曉史義的目的。
章學誠去世後,其著述大約形成兩個版本系統。一是大梁本《文史通義》系統,大梁本是指章學誠之子章華绂于光緒十二年(1832)刊刻于開封的《文史通義》八卷、《校雠通義》三卷。此後,伍崇曜刻于鹹豐元年(1851)的《粵雅堂叢書》本、補刊于同治十二年(1873)的浙江書局本,以及章學誠曾孫章季真刻于光緒三年(1877)的貴陽本,皆是在大梁本基礎上翻刻、補刊而成。因此,筆者将以上諸本統稱為“大梁本《文史通義》系統”。二是一九二二年劉承幹嘉業堂刊《章氏遺書》,該本以沈曾植家藏鈔本為底本,并益以《和州志》《永清縣志》《信摭》等,彙編而成為迄今收錄章氏著作最備之版本。
專家點評
他把闡發史意作為《文史通義》一書的最高宗旨,也是與當時的學術背景有關的。自清初顧炎武開創考據學派之後,由于清政府采取了高壓與懷柔相結合的文化專制主義政策,至乾嘉時代,考據學者們終日埋頭典籍,不問世事,竟為無用的魚蟲之學。
章學誠認為,這是從明人無本空談的一個極端又走到了過分強調征實的另一個極端了,因而對考據學風應當有所矯正,提倡發揮自己的主觀見解,他在《與汪龍莊書》一文中說,“今日學者風氣,征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時,而不能抽絲。拙撰《文史通義》,中間議論開辟,實有不得已而發揮,為千古史學辟其蓁蕪。”表明自己撰寫《文史通義》,以史意為宗旨,也有矯正時下考據學風之意。
清初進步思想家黃宗羲開創了浙東史學學派。浙東史學具備兩個最鮮明的特點:即倡導經世緻用之學和注重史學的研究。黃氏死後,浙東史學的影響雖不及考據學派,但代有傳人,脈系不絕。至乾嘉時代,章學誠成為這一派的主要代表。學誠着《文史通義》,以史意為宗旨,不僅繼承了浙東史學注重史學研究的優良傳統,而且在史學領域創立了自己的尚意史學理論體系,對清代史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因而後世稱他為浙東史學的殿軍,不是沒有一定道理的。
唐代著名史學理論家劉知幾撰寫的《史通》,在中國史學批評史上樹立了第一個高峰,後人若要趕上或超過他,就必須尋找到前人遺留下的空隙,并以此為突破口,創立自己的理論體系,決不能走前人走過的路。當章學誠青年時就在史學理論方面嶄露頭角,人們把他與劉知幾相比,他不但不高興,反而辯駁道:“吾于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拟吾于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正是因為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一書中大力倡導史意,言劉知幾所未言,才使他得以在中國史學批評史上樹立起第二個高峰,真正能夠做到與劉知幾比肩齊名。
思想體現
首先,扶持世教,匡正人心。他在《上尹楚珍閣學書》一文中說:“學誠讀書着文,恥為無實空言,所述《通義》,雖以文史标題,而于世教民彜,人心風俗,未嘗不三緻意,往往推演古今,竊附詩人之義焉。”學誠在這裡說的“世教”,當然是指儒家的仁義道德學說,這正是他的曆史局限所在,不過我們還是應當辯證看待這個問題。章學誠的這一觀點,在政治上雖然是消極的,但在學術上卻具有進步意義。
其次,扭轉僵化的考據學風。這點前文已有論述。
再次,對考據學以外的其他不良文風進行揭露和抨擊。章學誠在《又與朱少白書》一文中說:“鄙着《通義》之書,諸知己者許其可與論文,不知中多有為之言,不盡為文史計者,關于身世有所枨觸,發憤而筆于書,嘗謂百年而後,有能許《通義》文辭與老杜歌詩同其沉郁,是仆身後之桓譚也。《通義》書中《言公》、《說林》諸篇,十餘年前舊稿,今急取訂正付刊,非市文也,蓋以頹風日甚,學者相與離蛴攘臂于桎梏之間,紛争門戶,勢将不可已也。得吾說而通之,或有以開其枳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或于風俗人心不無小補欤!”
《文史通義》還為中國方志學奠基。該書外篇四至六都是方志論文。章氏雖長于史學,但從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學理論,用于編修方志的實踐中。編修方志在他一生活動中占有相當重要地位,并使他成為方志學建立的極其重要人物。梁啟超把他譽為我國“方志之祖”、“方志之聖”。
78年代全國修志熱潮興起後,他的方志學說還被用來當作啟蒙理論學習,《文史通義》也成為非談不可、非讀不行的熱門了。但該書内容龐雜,結構松弛,又缺少中心議題,各篇之間可以說互不關聯,這也許是因為作者一生生活極不安定,全部著作幾乎都寫于“車塵馬足之間”的緣故。
文本選讀
文德
凡言義理,有前人疏而後人加密者,不可不緻其思也。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學者所宜于深省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辭立其誠”,孟子嘗論“知言”“養氣”,本乎集義,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源”,皆言德也。
今雲未見論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内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凡為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為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
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習鑿齒為《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通鑒》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誤于先,而司馬再誤于其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于優也。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鑒》者,殆于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于九原,肯吾心服否邪?
陳氏生于西晉,司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讓,将置君父于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統也。(此說前人已言。)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隐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為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況生千古以後乎?聖門之論恕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道大矣。今則第為文人,論古必先設身,以是為文德之恕而已爾。
韓氏論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氣于水,言為浮物。柳氏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夫諸賢論心論氣,未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殺,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
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于稼穑也。夫識生于心也,才出于氣也。學也者,凝心以養氣,煉識而成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浮易弛。主敬者,随時檢攝于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緝熙敬止,聖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為義也廣矣。今為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為文德之敬而已爾。
文理
偶于良宇案間,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為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宇,啞然失笑,以謂己亦厭觀之矣。其書雲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标識,各為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為全篇結構,若者為逐段精彩,若者為意度波瀾,若者為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于拳服揣摩,号為古文秘傳。
前輩言古文者,所為珍重授受,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雲:“此如五祖傳燈,靈素受箓,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譏為野狐禅也。餘幼學于是,及遊京師,聞見稍廣,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非珍之也。”
文集
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闾裡,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為書,家存一說者也。(劉向校書,叙錄諸子百家,皆雲出于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無私門著述之征也。馀詳外篇。)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
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苟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于其徒,(諸子俱有學徒傳授,《管》《晏》二子書,多記其身後事,《莊子》亦記其将死之言,《韓非·存韓》之終以李斯駁議,皆非本人所撰,蓋為其學者,各據聞見而附益之爾。)則其說亦遂止于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
兩漢文章漸富,為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即《賈子書》。唐《集賢書目》始有《新書》之名。)相如詞賦,但記篇目:(《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次《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後,而叙錄總雲,《詩賦》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蓋各為一家言,與《離騷》等。)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彙次諸體,裒焉而為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
然範、陳二史,(《文苑傳》始于《後漢書》。)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雲所著詩、賦、碑、箴、頌、诔若幹篇,而不雲文集若幹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隋志》:“别集之名,《東京》所創。”蓋未深考。)自摯虞創為《文章流别》,學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為别集;則文集之名,實仿于晉代。(陳壽定《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雲《諸葛亮故事》,其篇目載《三國志》,亦子書之體。
而《晉書·陳壽傳》雲,定《諸葛集》,壽于目錄标題,亦稱《諸葛氏集》,蓋俗誤雲。)而後世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擾之文,亦泛濫橫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是誠劉《略》所不能收,班《志》所無可附。而所為之文,亦矜情飾貌,矛盾參差,非複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
夫治學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興,誠僞之判也。勢屢變則屢卑,文愈繁則愈亂。苟有好學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因散而求會同之歸,則三變而古學可興。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喪實,二缶猶且以鐘惑,況滔滔之靡有底極者。
昔者,向、歆父子之條别,其《周官》之遺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别其家,合天下學術而守于官,非曆代相傳有定式,則西漢之末,無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藝文志》有錄無書者,亦歸其類,則劉向以前必有傳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确據,當是劉氏失其傳。)班《志》而後,紛紛著錄者,或合或離,不知宗要,其書既不盡傳,則其部次之得失,叙錄之善否,亦無從而悉考也。
荀勖《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贊,與汲冢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為文翰志,而介于諸子軍書之間,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尚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為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仿于蕭梁,而古學源流,至此為一變,亦其時勢為之也。
嗚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窮而有類書。學者貪于簡閱之易,而不知實學之衰;狃于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傑之士,從狂瀾既倒之後,而欲障百川于東流,其不為舉世所非笑,而指目牽引為言詞,何可得耶?
且名者,實之賓也。類者,例所起也。古人有專家之學,而後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而後有專門之授受。(鄭樵蓋嘗雲爾。)即類求書,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雖三墳五典,可坐而緻也。自校雠失傳,而文集類書之學書,一編之中,先自不勝其龐雜;後之興者,何從而窺古人之大體哉?夫《楚詞》,屈原一家之書也。
自《七錄》初收于集部,《隋志》特表《楚詞》類,因并總集别集為三類,遂為著錄諸家之成法。充其義例,則相如之賦,蘇、李之五言,枚生之《七發》,亦當别标一目,而為賦類、五言類、《七發》類矣。總集别集之稱,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濫,實始詞賦不列專家,而文人有别集也。《文心雕龍》,劉勰專門之書也。
自《集賢書目》收為總集,(《隋志》已然。)《唐志》乃并《史通》《文章龜鑒》《史漢異義》為一類;遂為鄭略、馬《考》諸子之通規。(《鄭志》以《史通》入通史類,以《雕龍》入《文集》類。夫漁仲校雠,義例最精,猶舛誤若此,則俗學之傳習已久也。)充其義例,則魏文《典論》,葛洪《史鈔》,張骘《文士傳》,(《典論·論文》如《雕龍》,《史鈔》如《史漢異義》,《文士傳》如《文章龜鑒》,類皆相似。)亦當混合而入總集矣。
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論》,子類也。《史鈔》、《文士傳》,史類也。)其例之混實由文集難定專門,而似者可亂真也。著錄既無源流,作者标題,遂無定法。郎蔚之《諸州圖經集》,則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慶《寶章集》,則經部小學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玄覺《永嘉集》,則子部釋家而有集名矣。
(《唐志》所收。)百家雜藝之末流,識既庸暗,文複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數,本非集類,而紛紛稱集者,何足勝道?(雖曾氏《隆平集》,亦從流俗,當改為傳志,乃為相稱。)然則三集既興,九流必混,學術之迷,豈特黎丘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篇卷
《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詩》曰:“出言有章。”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着之于書,則有簡策。标其起訖,是曰篇章。孟子曰:“吾于《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是連策為篇之證也。《易·大傳》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為篇之證也。左氏引《詩》,舉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則曰某章雲雲。是篇為大成,而章為分阕之證也。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遠可達而已。篇章簡策,非所計也。
後世文字繁多,爰有校雠之學。而向、歆著錄,多以篇卷為計。大約篇從竹簡,卷從缣素,因物定名,無他義也。而缣素為書,後于竹簡,故周、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第彼時竹素并行,而名篇必有起訖;卷無起訖之稱,往往因篇以為之卷;故《漢志》所著幾篇,即為後世幾卷,其大較也。然《詩經》為篇三百,而為卷不過二十有八;《尚書》、《禮經》,亦皆卷少篇多,則又知彼時書入缣素,亦稱為篇。
篇之為名,專主文義起訖,而卷則系乎綴帛短長,此無他義,蓋取篇之名書,古于卷也。故異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聞用以标起訖。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後》之傳,篇長卷短,則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後,訖于隋、唐,書之計卷者多,計篇者少。著述諸家,所謂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謂一篇;則事随時變,人亦出于不自知也。惟司馬彪《續後漢志》,八篇之書,分卷三十,割篇徇卷,大變班書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傳,失古人之義矣。
(《史》、《漢》之書,十二本紀、七十列傳、八書、十志之類,但舉篇數,全書自了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傳》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為一,總卷之數,仍與相符,是以篇之起訖為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馬彪以八志為三十卷,遂開割篇徇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實亦不正矣。
歐陽《唐志》五十,其實十三志也,年表十五,其實止四表也。《宋史》列傳二百五十有五,《後妃》以一為二,《宗室》以一為四,李綱一人,傳分二卷,再并《道學》《儒林》,以至《外國》《蠻夷》之同名異卷,凡五十馀卷,其實不過一百九十馀卷耳。)
至于其間名小異而實不異者,道書稱?,即卷之别名也,元人《說郛》用之。蒯通《隽永》稱首,則章之别名也,梁人《文選》用之。此則标新著異,名實故無傷也。唐、宋以來,卷軸之書,又變而為紙冊;則成書之易,較之古人,蓋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謂簡帙繁重,不可合為一篇者,(分上中下之類。)今則再倍其書,而不難載之同冊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為十卷,今人不過三四卷也。
自宋以來,分卷遂長。以古人卷從卷軸,勢自不能過長;後人紙冊為書,不過存卷之名,則随其意之所至,不難钜冊以載也。以紙冊而存缣素為卷之名,亦猶漢人以缣素而存竹簡為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計文之起訖矣,是終古不可改易,雖謂不從竹簡起義可也。卷則限于軸之長短,而并無一定起訖之例。今既不用缣素而用紙冊,自當量紙冊之能勝而為之界。其好古而标卷為名,從質而标冊為名,自無不可;不當又取卷數與冊本,故作參差,使人因卷尋篇,又複使人挾冊求卷,徒滋擾也。
夫文之繁省起訖,不可執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寂寥短篇,亦可自為一書,孤行于世。蓋方策體重,不如後世片紙,難為一書也。)則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連編,勢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冊而分之,使人多一檢索于離合之外,又無關于義例焉,不亦擾擾多事乎?故著書但當論篇,不當計卷。(卷不關于文之本數,篇則因文計數者也。故以篇為計,自不憂其有阙卷,以卷為計,不能保其無阙篇也。)必欲計卷,聽其量冊短長,而為铨配可也。
不計所載之冊,而铢铢分卷,以為題簽著錄之美觀,皆是泥古而忘實者也。《崇文》、《宋志》,間有着冊而不詳卷者。明代《文淵閣目》,則但計冊而無卷矣。是雖著錄之阙典,然使卷冊苟無參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書,自不宜強改。)
天喻
夫天渾然而無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黃道、赤道,曆家強名之以紀數爾。古今以來,合之為文質損益,分之為學業事功,文章性命。當其始也,但有見于當然,而為乎其所不得不為,渾然無定名也。其分條别類,而名文名質,名為學業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并者,皆因偏救弊,有所舉而诏示于人,不得已而強為之名,定趨向爾。
後人不察其故而徇于其名,以謂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紛紛有入主出奴之勢焉。漢學宋學之交譏,訓诂辭章之互诋,德性學問之紛争,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學業将以經世也,如治曆者,盡人功以求合于天行而已矣,初不自為意必也。其前人所略而後人詳之,前人所無而後人創之,前人所習而後人更之,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于《堯典》,太初曆法不可同于《月令》,要于适當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後,而身為冢宰,故制作禮樂,為一代成憲。
孔子生于衰世,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當處士橫議之時,故力距楊、墨,以尊孔子之傳述。韓子當佛老熾盛之時,故推明聖道,以正天下之學術。程、朱當末學忘本之會,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其事與功,皆不相襲,而皆以言乎經世也。故學業者,所以辟風氣也。風氣未開,學業有以開之。
風氣既弊,學業有以挽之。人心風俗,不能曆久而無弊,猶羲和、保章之法,不能曆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補救,猶曆家之因其差而議更改也。曆法之差,非過則不及。風氣之弊,非偏重則偏輕也。重輕過不及之偏,非因其極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趨風氣而為學業,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環天度數,盡春秋中國都邑。夫中國在大地中,東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屬之占驗,未嘗不應,此殆不可以理推測,蓋人定之勝于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時,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生克。夫年月與時,并不以甲子為紀,古人未嘗有是言也。
而後人既定其法,則亦推衍休咎而無不應,豈非人定之勝天乎?《易》曰“先天而天弗違”,蓋以此也。學問亦有人定勝天之理。理分無極太極,數分先天後天,圖有《河圖》、《洛書》,性分義理氣質,聖人之意,後賢以意測之,遂若聖人不妨如是解也。率由其說,亦可以希聖,亦可以希天。豈非人定之勝天乎?尊信太過,以謂真得聖人之意固非,即辨駁太過,以為諸儒诟詈,亦豈有當哉?
師說
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者也。”又曰:“師不必賢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又曰:“巫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而因怪當時之人,以相師為恥,而曾巫醫百工之不如。韓氏蓋為當時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師之究竟也。《記》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親、師也。”此為傳道言之也。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
業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且解者之為師,固然矣;然與傳道有間矣。巫醫百工之相師,亦不可以概視也。蓋有可易之師,與不可易之師,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語矣。知師之說者,其知天乎?蓋人皆聽命于天者也,天無聲臭,而俾君治之。人皆天所生也,天不物物而生,而親則生之。人皆學于天者也,天不諄諄而誨,而師則教之。然則君子而思事天也,亦在謹事三者而已矣。
人失其道,則失所以為人,猶無其身,則無所以為生也。故父母生而師教,其理本無殊異。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東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親也,理勢不得不然也。若夫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經師授受,章句訓诂;史學淵源,筆削義例;皆為道體所該。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帛之外,别有心傳,口耳轉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譜系不可亂也。
此則必從其人而後受,苟非其人,即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學問專家,文章經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傳。此亦至道所寓,必從其人而後受,不從其人,即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苟如是者,生則服勤,左右無方,沒則屍祝俎豆,如七十子之于孔子可也。至于講習經傳,旨無取于别裁;斧正文辭,義未見其獨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從甲不終,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告,乙亦可詢;此則不究于道,即可易之師也。
雖學問文章,亦末藝耳。其所取法,無異梓人之惎琢雕,紅女之傳絺繡,以為一日之長,拜而禮之,随行隅坐,愛敬有加可也。必欲嚴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義,則責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
巫醫百工之師,固不得比于君子之道,然亦有說焉。技術之精,古人專業名家,亦有隐微獨喻,得其人而傳,非其人而不傳者,是亦不可易之師,亦當生則服勤,而沒則屍祝者也。古人飲食,必祭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況成我道德術藝,而我固無從他受者乎?至于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則觀所得為何如耳。所争在道,則技曲藝業之長,又何沾沾而較如不如哉?
嗟夫!師道失傳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見不可易之師;而觀于古今,中有怦怦動者,不覺冁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從,是亦我之師也。不見其人,而于我乎隐相授受,譬則孤子見亡父于影像,雖無人告之,夢寐必将有警焉。而或者乃謂古人行事,不盡可法,不必以是為屍祝也。夫禹必祭鲧,尊所出也。兵祭蚩尤,宗創制也。若必選人而宗之,周、孔乃無遺憾矣。人子事其親,固有論功德,而祧祢以奉大父者耶?
假年
客有論學者,以謂書籍至後世而繁,人壽不能增加于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書,如能五百年生,學者可無遺憾矣。計千年後,書必數倍于今,則亦當以千年之壽副之,或傳以為名言也。餘謂此愚不知學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雖假之以五千年,而猶不達者也。
學問之于身心,猶饑寒之于衣食也。不以飽暖慊其終身,而欲假年以窮天下之衣食,非愚則罔也。傳曰:“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人之異于物者,仁義道德之粹,明物察倫之具,參天贊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若夫知覺運動,心知血氣之禀于天者,與物豈有殊哉?夫質大者所用不得小,質小者所資不待人,物各有極也。
人亦一物也。鲲鵬之壽十億,雖千年其猶稚也。蟪蛄不知春秋,期月其大耋也。人于天地之間,百年為期之物也。心知血氣,足以周百年之給欲,而不可強緻者也。
夫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聖人,人道之極也。人之學為聖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聞待十倍百倍之年也。一得之能,一技之長,亦有志學之始,與不逾矩之究竟也。其不能至于聖也,質之所限也,非年之所促也。顔子三十而夭,夫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痛其不足盡百年之究竟也。
又曰:“後生可畏。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不足畏。”人生固有八十九十至百年者,今不待終其天年,而于四十五十,謂其不足畏者,亦約之以百年之生,度其心知血氣之用,固可意計而得也。五十無聞,雖使更千百年,亦猶是也。
神仙長生之說,誠渺茫矣。同類殊能,則亦理之所有,故列仙洞靈之說,或有千百中之十一,不盡誣也。然而千歲之神仙,不聞有能勝于百歲之通儒,則假年不足懋學之明征也。禹惜分陰,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将至。”又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
蓋懼不足盡百年之能事,以謂人力可至者,而吾有不至焉,則負吾生也。蟪蛄縱得鲲鵬之壽,其能止于啾啾之鳴也。蓋年可假,而質性不可變;是以聖賢愛日力,而不能憾百年之期蹙,所以謂之盡性也。世有童年早慧,誦讀兼人之倍蓰而猶不止焉者,宜大異于常人矣。及其成也,較量愚柔百倍之加功,不能遽勝也。
則敏鈍雖殊,要皆畫于百年之能事,而心知血氣,可以理約之明征也。今不知為己,而骛博以炫人,天下聞見不可盡,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盡之生,而逐無窮之聞見;以一人之身,而逐無端之好尚;堯、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遍物。堯、舜之仁,不遍愛人。”今以凡猥之資,而欲窮堯、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于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
族子廷楓曰:“叔父每見學者,自言苦無記性,書卷過目辄忘,因自解其不學。叔父辄曰:‘君自不善學耳。果其善學,記性斷無不足用之理。書卷浩如煙海,雖聖人猶不能盡。古人所以貴博者,正謂業必能專,而後可與言博耳。蓋專則成家,成家則已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己者,雖锱铢不遺。
不切己者,雖泰山不顧。如此用心,雖極鈍之資,未有不能記也。不知專業名家,而泛然求聖人之所不能盡,此愚公移山之智,而同鬥筲之見也。’此篇蓋有為而發,是亦為誇多鬥靡者,下一針砭。故其辭亦莊亦諧,令人自發深省,與向來所語,學者足相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