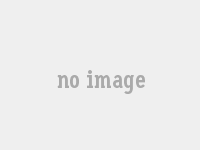内容簡介
《綠房子》的故事發生在相距很遠的兩處地方,即位于秘魯海邊沙漠地區的皮烏拉市和遠在亞馬遜流域心髒地帶的能夠經商和傳教的聖瑪麗亞·德·聶瓦鎮。故事的象征物就是那非常出名的,由外地人安塞爾莫建造的享樂中心--綠房子。皮烏拉市由一個落後的小城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城市,而森林地區仍處在原始狀态中,仍然是國内外冒險家活動的舞台。他們勾結官府,占島為王,殺人越貨,對土著民族進行掠奪和剝削,《綠房子》涉及了整個秘魯北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和社會上的各式各樣的人物。
作品中的秘魯濃縮地反映了曆史,其中,土著首領胡姆的故事再現拉美殖民的場景。文本中塑造了幾個形象:伏屋--主張殖民主義的冒險家;鎮長列阿基德--使用政治暴力機器鎮壓、剝削土著居民的大莊園主;傳教所嬷嬷--強行"收養"土著印第安"孤兒",實則為後殖民統治的"幫兇"。胡姆,是個代表土著印第安人反抗政府和軍警以及奸商剝削、壓迫的人物形象。作為印第安瓊丘族的首領,胡姆在"掃盲教師"告知不等價交換的欺詐性後,勇敢地帶領部族放抗鎮長的殘酷盤剝和警匪的無盡搶掠。
軍警的騷擾,官員的拷打侮辱以及土匪的籠絡欺騙都沒有擊垮他,可當他明白"官官相護"的黑暗時,精神崩潰。作者在他身上用的筆墨不多,但這個将"屁魯"挂在嘴邊,儀态莊重的首領處處代言着作者對殖民曆史事件的批判态度:外國殖民主義者的精神攻略是造成拉美落後愚昧的重要根源;獨裁統治和官場腐敗是社會進步的主要障礙。
如果說冒險家和政客赤裸裸的"前殖民式"掠奪是野蠻的,那"後殖民式"的所謂的"文明教化"的确顯得溫文爾雅。德聶瓦小鎮傳教所的嬷嬷們認為對土著孩子的強制教育是一種恩賜:"你(指鮑妮法西娅)那時就像一隻小獸,我們給你吃的、住的,給你起名字,還給你上帝⋯⋯"可是,事實上"被拯救者"卻覺得境遇可憐:"兩人(指被搶來的土著女孩)⋯⋯沾滿塵土、草屑,無疑還有虱子。嬷嬷的剪刀和滾燙的紅色殺菌水都還沒接觸到她們的頭發呢⋯⋯
在那亂草般的頭發下,兩個互相擁抱着的小身體開始哆嗦,就像受了驚的大手猴被關在籠子裡那樣。"無論哪一種殖民方式對于承受對象而言都足一個被迫接受與激進抗拒混雜的痛苦過程。他通過小說裡的人物向自以為是的文明世界發問:"為什麼孤兒偏偏要回到那肮髒的部落裡去?""教她們學文化是好的,但為什麼要強迫呢?"這無疑是在質疑殖民主體所制定的文化價值觀參照結構。
鮑妮法西娅,一個森林土著的女兒,西班牙教會"文明的教化"使得她被迫離開了父母及賴以生存的土地。而"接受教化"的真相是:聖瑪利亞·德·聶瓦鎮上修道院的修女們開辦了一所感化學校,每隔一段時間,她們就要在軍隊的幫助下,搜捕未成年土著女孩入學并重新接受命名和教育。幾年全封閉的準軍事化管理讓她們學會了西班牙語和許多聞所未聞的"文明習俗",女孩們被培養成"文明人",有償或無償送給上等人做女傭。
這是一種典型的對于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話語暴力,不僅使殖民地文化殖民化,更重要的是,宗主國的文化觀念使被殖民的民族産生一種被強制的文化認同感。鮑妮法西娅的話語不多,表面上是個默默"認同"文化殖民教化"合格品",但文中的幾處描寫都能使讀者看到她自己特意保留的土著印記:放跑了不堪虐待的土著小夥伴,她在被審訊時反駁安赫利卡嬷嬷對她的辱罵:"您别叫我傻瓜。親愛的嬷嬷,她沒有偷我的鑰匙。
是我給她們開的門";學習穿代表"文明"的高跟鞋時,對于痞子們的調侃,她說"誰也不會為自己的故鄉感到羞恥",然後從容不迫地脫掉鞋子;面對丈夫的提高嗓門的訓斥,她既不回答也不動,"一記清脆的耳光呼嘯着打過去,她閃也不閃一下"⋯⋯這個女性所展現的土著居民的堅強、善良、自尊和誠實不是任何強權手段可以任意抹去的。
這個人物的翅造體現出作者對于統治結構中被邊緣化的"他者"的研究和關注。這部小說讀者看到的主要是略薩的反殖民思想,但同時也難以避免的發現内容裡潛藏着後殖民話語。"一陣咕哝聲打斷了她(指安赫利卡嬷嬷),好像在倉庫裡藏着一個動物,這動物突然發起怒來,在黑暗中又哼又叫,叽叽呀呀,時而高昂,時而吱吱嘎嘎,像是在撒野,也仿佛在挑戰。
"以上是鮑妮法西亞為證明自己确實向孤兒們學會了"土話"而進行的"表演",文本中對于土著居民話語的描寫多處都用了諸如此類"非人化"的叙述。其實這種"矛盾"的存在可以理解。作為殖民主義的批判主體擁有顯而易見的"特權"從而無法"代表"被壓迫者,且本身身份在中心與邊緣之間模糊,他所處的環境決定了他為第三世界"邊緣"言說時總要混合一點來自"中心"的雜音。
作者還運用了許多手法來豐富小說的多面體藝術特征,影視技巧的運用就像千絲萬縷的絲線,将小說的各個部分結成網絡,并在各個部分之間搭建了條條通道,使得《綠房子》的内在結構實現了立體化。意識流手法模糊了時空界限、想象與現實的分野,使得單個情節的叙述也變成多層的、立體的,從而使多面體大廈的内部格局呈現為立體結構,和《綠房子》的總體框架融合為一體。精彩的對話藝術是對多面體結構的補充和具體化。
多面體立體結構不僅是《綠房子》的外部框架,而且是從部分到整體,從内而外一緻的形式特征。《綠房子》的結構形式中寄寓了作者對生活的理解和對文學的信念,對這種結構方式的分析顯示了作者的真實觀和文學創作理念。
作品目錄
前言
本書主要人物表
附:故事發生地點示意圖
綠房子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尾 聲
創作背景
《綠房子》選取的時間是20世紀20至60年代的秘魯殖民統治時期北部(包括沿海地區、安第斯山區和森林地區)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和人物為背景。在這片土地上不斷上演着西方文明對土著的殘酷掠奪與土著奮力反抗、維護家園的鬥争,印第安"野性"文明拒絕被西方"先進"文明同化的抗争,超越倫理道德的愛情,還有政界的黑暗腐敗等。從神父、政客到妓女、二流子,從外國冒險家、修女到土著居民、妓院老闆,各色各樣的人物穿梭其中。作者将生活在這繁雜社會中人物的複雜經曆主要用五條情節來處理:
1、鮑妮法西亞(孤女)與警長利杜馬的愛情故事;
2、伏屋的匪盜故事;
3、安塞爾莫與綠房子的故事;
4、土著首領胡姆與軍隊、政客及中間人之間掠奪與抗争的故事;
5、包括利杜馬在内的四個二流子的故事。五個故事分别發生在皮烏拉城、聖母瑪利亞·德·聶瓦鎮和瑪臘尼昂河各支流上。
主要人物
鮑妮法西娅
鮑妮法西娅,一個森林土著的女兒,西班牙教會“文明的教化”使得她被迫離開了父母及賴以生存的土地。
一、自我造就的妓女
鮑妮法西娅最初在修道院裡當女仆,由于放走了20多個土著女孩而被嬷嬷趕出修道院,之後被拉麗達收養,經拉麗達引薦後又與利杜馬結婚,利杜馬殺人被捕入獄,正懷有身孕的鮑妮法西娅無依無靠,沒有能力賺錢,經何塞費諾引誘而成為妓女,改名塞爾瓦蒂卡,從此賣淫為生。鮑妮法西娅成為妓女的時候獲得了重新命名。命名這種儀式使得人獲得重生,一方面它隔絕了父輩的文化,是一種弑父心理的外化;另一方面它割斷了自己與過去的聯系,打破了自我。
但關鍵問題卻在于究竟是自我命名還是他人命名。她是如此可悲,她的命名是由誘騙她的二流子何塞費諾完成的。男人替無知的女人選擇了道路,女人乖巧地将自己的命運交付與他人。何其可悲,女人已經低微到塵埃裡了,生命之舟操控于男人之掌,生命之流源于男人之海。
鮑妮法西娅的人生是一段被奴役被抛棄的曆史。首先在故鄉,作為一個瓊丘人,她被土著父母抛棄;而在修道院裡,她雖是出于愛心而放走孩子們,卻再一次被宗教抛棄;之後獻身于婚姻,企圖獲得婚姻的庇護,即使她在家庭中完全是一個失語者,即使遭到丈夫不斷地暴力對待,她仍舊隐忍着,之後丈夫被抓,她又一次被婚姻抛棄;二流子何塞費諾給予她堅如磐石、纏綿悱恻的承諾,可最終,看似千金不換的愛情僅僅是男人一時欲望沖動的代名詞。
未曾有人真正地給予她過愛情,沒有愛,無論在作警長的妻子,還是作二流子的情婦,都未曾有人拿一顆真心換取另一顆真心,都未曾有一個男人拿一生的承諾換取一個女人的一生。鮑妮法西娅從女仆成為他人之妻最終淪為妓女,這一過程中什麼都在變,但被人奴役的本質沒有變:在修道院裡被嬷嬷們奴役、作他人之妻時被丈夫奴役、最終淪為妓女,滑到痛苦之深淵。她的人生就是一段被奴役的曆史。
最終,萬念俱已成灰,她修正自己的價值觀,遷就于他人,失去自我——自己将自己抛棄了。一個女人,如若與世界格格不入,完全可以選擇一種“自絕于塵世”的方式,她完全可以回到土著部落裡過回自耕自農的生活,可她自欺欺人地以為自己回不去了。她天真得相信,已經接受了現代化熏陶的自己再也回不到最初的部落了,就這樣,她無恥且無知得成為原始文明與現代文明較量之下的虛假的犧牲品。‘
最終在故事結尾的地方,塵埃落定,皆成定局,二流子何塞費諾無恥地叫她嫂子,她憤怒了,但隻是轉瞬即逝的憤怒,隻是弱者羸弱而無力地低吟:“我不是你的嫂子”,塞爾瓦蒂卡說道,“我是個婊子,是個揀來的孤兒”。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她的丈夫利杜馬最終出獄,卻終日渾渾噩噩,無所事事,靠着塞爾瓦蒂卡賣身的錢生活,但同時瞧不起養活自己的“妓女”。
妓女出售的不僅僅是有形的身體,還有她們無形的尊嚴與人格。在她失去尊嚴與人格的同時也被一切所摒棄:“妓女是替罪羊,男人釋放自己的卑劣欲望,發洩在她身上,然後否定她……妓女沒有人的權利,在她身上集中了女性奴隸處境的所有形式”。
二、社會造就的妓女
秘魯社會轉型時期的“人吃人的本質”:“你整我,我整你,讓人家整的人就會自己倒黴。一無政府保障、二無良好出身、三無工作機會的女人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出路隻有兩條:要麼嫁人,要麼堕落。婦女的經濟權利得不到任何保障,社會也并沒有給婦女提供任何工作的機會。
正是這樣的社會形态,導緻女人必須依賴于男人才能生活。而正是這緻命的制度,使得男人無需尊重女性,無需給予女性應有的愛情,無需給予承諾以及婚姻的保障。秘魯的軍事獨裁政治直接導緻秘魯的封閉與腐敗,封閉便意味着觀念的封閉,秘魯社會遍地都是不幸福的女性,一半是社會在助纣為虐,一半是她們自己在制造悲劇。
作品鑒賞
主題思想
20世紀初的秘魯社會,正籠罩在軍事政治獨裁的巨大霧霾中,新舊觀念沖擊着這個正處于轉型期的社會。
對外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對内反對軍事獨裁統治和莊園制一直是拉丁美洲人民反抗的主題。貧富懸殊,階級矛盾尖銳造成了社會嚴重的不公正、不公平現象。而土著人則是受害者中最嚴重的群組。而在這樣一個複雜的社會背景下,女性完全是從屬性的、是社會中的他者,女性的身體則淪為男人發洩欲望的商品。
《綠房子》創作于1965 年,表面上是一部"青樓"興衰史,實際上是那個時期新舊觀念、不同的價值取向之間鬥争沖撞的曆史,小說中矛頭直指秘魯的社會現實:拉丁美洲雖然獨立了,卻一直遭受帝國主義的霸權、殖民主義的強權和軍事獨裁的政權這三座大山的壓迫。對于女性來說,傳統的天主教、男尊女卑思想仍然根深蒂固。
結構特征
一、多面體的結構形态與拼圖式閱讀
《綠房子》的結構曾被稱為聯通器法......"中國套盒式"和"古羅馬廊柱式",這些提法從不同的側面對《綠房子》的結構加以概括。其實,《綠房子》的結構更像是一個螺旋上升的多面體。為了便于論述,首先對《綠房子》的結構做一個剖析。
《綠房子》分為四個部分和一個尾聲,每部前有一段序,第一部和第三部各分為四章,第二部和第四部各分為三章。第一、二部的每章又分為五節,第三、四部的每章分為四節,全書講述了五個故事,每節講述一個故事的一段。用A/B/C/D/E代表五個故事,用數字代表故事的發展階段,那麼五個故事都被劃分為十四段,經曆了從Al/Bl/C1/D1/E1到A14/B14/C14/D14/E14的發展過程。
每一部的序主要叙述聖瑪麗亞·德·聶瓦鎮和聖地亞哥河上發生的故事,故事A是關于鮑妮法西亞的,故事B交待伏屋的一生,故事C講述安塞爾莫的一生和綠房子的興衰史,故事D講述胡姆的反抗,故事E講述皮烏拉城四個二流子的故事。到第三、四部中,胡姆被伏屋收留,故事D與E就合二為一了。尾聲對五個故事的結局作了交待。
整體看來,這一結構像一個螺旋上升的多面體,五條叙事線ABCDE就像五條邊,每一條邊是同一個故事的延伸,但是小說中的叙事并不是順着這五條邊直接向上延伸,而是沿着A-B-C-D-E的順序轉一圈回到A的位置再向上延伸進入上一層,如第一部第一章就包括A/B/C/D/E五個故事各一段,即A1/B1/C1/D1/E1。每一章都是由五個故事或四個故事各一個段落構成的。每一節像多面體結構的一層,叙事就在螺旋中上升,形成多面體的立體叙事結構。
字母和數字的排列是清晰整齊的,但作者對切割成小塊的故事的安排卻是立體的、生活化的,表現為叙事時間與故事時間的錯位,故事的發展和叙事的順序不一緻。即申丹所說的叙述時序與事态時序不一緻,"無論叙述時序如何錯亂複雜,讀者一般能重新建構出事态時序,但在《綠房子》裡這種建構卻需要讀者閱讀中耐心等待較長時間,并主動探索積極建構。下面以鮑妮法西亞的經曆為例展示一下這種錯位:故事A和E因鮑妮法西亞和利杜馬結婚回皮烏拉而交叉、合流,但叙事并不是沿着A1到A14的順序進行,然後又從E1到E14延續下去的。
故事A和E是同時展開叙事的,若按照小說文本叙述時序閱讀,小女孩鮑妮法西亞被白人抓走、修女鮑妮法西亞被傳教所驅逐、鮑妮法西亞已經成為皮烏拉的妓女塞爾瓦蒂卡,這相差許多年的事情幾乎是同時讀到的。叙事時空的交錯使得故事原貌隐藏在重重雲霧之後,又不時露出一鱗半爪,随着閱讀的進一步深入才可以發現,A和E相互補充,前面和後面的叙述互為交待。直到讀到第二部第一章E5和A5,才明白鮑妮法西亞原來就是被抓來的瓊丘女孩。而直到第四部讀完,才能解答第一部已出現的懸念:何塞費諾為什麼懼怕利杜馬。閱讀不斷深入,懸念一個個解決,伏筆随之一個個埋下,新的懸念又一個個橫空産生,使讀者産生新的閱讀期待。
巴爾加斯·略薩的小說使讀者感到有趣的挑戰,因為叙事是支離破碎的,叙述者并非全知全能。如果用熱奈特的理論進行分析,《綠房子》常常采用一種内聚焦的叙事方式,以作品中人物的視角觀察和叙述,并不斷切換視角,試圖從不同人物出發來觀照生活,因此,呈現出不全面的、片段的、跳躍性的叙事特征。作品中的五個故事被切割成許多情節塊,作品就是一個由許多闆塊組成的多面體,但這個多面體表面是不平整的、不光滑的、不規則的,因為闆塊之間有相互聯系但又獨立存在,塊與塊之間留有很大空隙,需要讀者的積極閱讀來加以補充。
讀者在這裡就是作品的有機組成部分,沒有讀者,《綠房子》就是不完整的,像淩亂的、雜陳的積木,隻有讀者思想與經驗的加人才能彌補文中的空白,形成完整的作品。這種閱讀就像拼圖,讀者不僅要運用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思想邏輯把各個闆塊安放在合适的位置,而且需要依靠自己的經驗和想象把空缺處補充完整。讀者的參與是構建這個多面體大廈的必要條件,否則就隻有多面體的外部框架結構,而内部卻無法溝通。在搭起了這個多面體的立體框架之後,作者還運用了許多手法來豐富小說的多面體藝術特征。
二、影視技巧與立體結構
影視藝術是一種立體的藝術形式,在《綠房子》的創作中,他已經引進了影視的一些表現技巧,來增強小說的立體結構效果。首先,通過不同場景的交叉切換推動情節發展,實現立體疊映效果。《綠房子》中許多場景的描寫接近于影視藝術的表現方式,有遠景,有近景,還有特寫,不同層次的叙事通過不同距離的場景表現出來,通過遠景近景的交叉、切換推動情節的發展。例如塞瓦約斯醫生為安東妮娅接生的場景突然切換為何塞費諾帶鮑妮法西亞去做流産的場景。
兩個場景表現的故事、時間、人物都相差甚遠,沒有必然的聯系,切換的完成僅僅由于兩個女人相似的痛苦;從安東妮娅被安塞爾莫吻着的嘴轉換為鮑妮法西亞被何塞費諾塞着的嘴,兩個場景來回切換,既各自渲染又互相對比,兩個不相關的場景疊加在一起,兩個情節同時交待清楚,用這種手法來達到以最少的筆墨傳達最大的信息量,最大限度地省略事件中間的關聯,以場景與場景的切換達到推動情節發展的目的。
場景與場景疊加的方式很容易達到構建立體畫面的效果,實現了叙述者最大限度的隐退,增強了叙事的客觀性,也在有限的篇幅内增加了叙事容量。而作者的态度卻在這種切換和對比中自然浮現。其次,遠景近景互為解釋,兩條情節線交織發展打造立體空間。以前面所談到的場景切換為例,它們之間沒有什麼直接聯系,僅僅因為表面的某些相似特征被安排在一起,這種手法實現了最大限度的簡約,就好像一棟樓房的上下兩層同時展現在讀者眼前,門窗相似,内容不同。同時,《綠房子》還有一些場景是互為說明、互相解釋的。
比如伏屋三人越獄的遠景與阿基裡諾與伏屋對話的近景不斷交叉顯現,互為解釋。和多數小說把回憶内容作為間接引語叙述的方式不同,巴爾加斯·略薩運用了影視技巧,不直接叙述越獄逃跑的情節,而是把它轉換為場景描寫,納入到對話的大語境中
使二者相互交織,遠景近景互相解釋,從而形成一個立體的空間,人物的活動在兩個場景中同時展開又互為關聯。越獄情節因為和對話場景的交叉出現而不斷被打斷,于是減少了逃跑現場的緊迫感,人物的感情也因為情節的一再中斷而有所節制。筆者認為,這種叙事方式和事後回憶的感覺是契合的,回憶情節的清晰性和情感的淡化被這種遠近景相互交織,兩條線索同時展開的立體結構诠釋得恰到好處,使人不得不驚歎于巴爾加斯·略薩叙事藝術的精妙。同時,這種叙事把主幹情節納入另一叙事語境之中,并不斷打斷其進程,從而達到了布萊希特叙事劇所追求的"陌生化"效果,利于達到讀者的理性閱讀,以實現巴爾加斯·略薩所主張的文學反映生活、幹預生活的目的。
除此之外,他還借鑒了影視作品中的其他技巧。例如,作者有時在場景之外加入旁白式的解說,使得showing和telling同時出現,互相解釋。對話、場景描寫和客觀叙述相結合,互為表裡,聽覺、視覺效果相互交織,使讀者對對話人和對話環境、談話内容進行全視角高屋建瓴的觀照,在閱讀中體驗到影視欣賞的全方位沖擊,從而多角度立體觀照故事情節。
如果讀者把《綠房子》的外部結構比喻為一個多面體的大廈,閱讀就像身處展覽館一樣在不同側面的展館問循序上升,那麼,影視技巧就像千絲萬縷的絲線,将小說的各個部分結成了一個網絡,如同聯通器,使得每一個展廳都變得通透,并為之搭建了條條通道。
三、意識流手法、多彩的對話與情節的立體表現方式
意識流手法是歐洲現代主義文學常用的一種藝術手法,巴爾加斯·略薩在《綠房子》中也運用了這種手法,打破時空界限,立體表現某些情節,以真實地表現特殊時刻人的感受,增強小說表現生活的真實性和生活的不确定性。"作者在寫到人物喝醉,垂死,或者極端驚恐緊張時,就使用了喬伊斯式的語言"。下面以安塞爾莫臨死之前對自己和安東妮娅共同生活的回憶為例做一分析。在這段回憶中,第一、第二、第三人稱交叉使用,其中以一般小說很少用的第二人稱為主,以另一個人--瀕臨死亡的安塞爾莫或者說已跳出軀殼的安塞爾莫的靈魂的口吻表現"你"--青年安塞爾莫與安東妮娅的"對話"。
這是有聲語言與無聲語言的交流,安塞爾莫的語言與他的行動及他猜想的安東妮娅的内心相交織,其中又以第一人稱、第三人稱的方式插入對綠房子妓女們語言和行動的描寫。"你"字在這裡運用得特别頻繁,但所指不同,有時站在垂死的安塞爾莫的角度指青年安塞爾莫,有時站在青年安塞爾莫的角度指托妮達安(東妮娅的愛稱),有時又用"你們"代表妓女們。同一個字由于視點的轉換,所指在不斷變換。
這是典型的内聚焦,随着視點的轉變内容在不斷地跳躍,而視點的不同卻被有意忽略了。這種意識流的表達方式恰恰契合了垂死者的思維方式,客體與主體不分,自己與他人不分,時間的先後,空間的不同都被淡化了、模糊了,此時所展現的完全是一種多時空多層次多維度的潛意識的立體狀态。
弗洛依德認為,在人的潛意識中,時間已經不再是空間的概念,而是一個質量的概念,過去與現在不分,現實與回憶不分。在垂死的安塞爾莫的意識中,過去與現在,現實與想象已經無法區分,他的靈魂在自己的世界中漂浮,這裡有他的回憶、他的夢想,也有他的希望,所有這一切都交織在一起,意識流手法在這裡的運用就很好地表現出了這種狀态,巴爾加斯·略薩以此表達他所理解的生活真實。
從表面上看,意識流手法的運用好像使叙事變成了線性的、單一的結構,其實,深入探究就會發現,意識流手法模糊了時空界限,使過去與現在相互交織,想象與現實互相交錯,而一個情節的叙述也變成了多層的、立體的。如果說影視技巧的運用使得《綠房子》的每個房間之間實現了相通,内部成為聯通器,那麼,意識流手法的運用就使得一些房間内部的格局也變為立體結構,和《綠房子》的總體框架融合為一體。
小說的其他方面也表現出這種多面性和立體性,如《綠房子》的對話形式。《綠房子》的對話形式多種多樣,有叙述與對話的交叉,多重對話的交叉,獨白與對話的交叉,還有不交待對話人,不以标點和分行做區分的對話波。一組對話可能因為一個相關話題、相關場景或相似氣氛而陡轉入叙述、獨自或另一組對話,有時甚至運用雙線并行對話的方式同時交待兩件無甚關系的事件。很多時候。作者對講話人不做交待,而是通過稱呼或談話内容讓人感知,有時候,對講話人稱謂的改變甚至成為情節發展的一種方式。
例如第二部的序中,堂胡利奧與堂法比奧在對話,對話人卻忽然變成了鎮長與堂胡利奧,這樣,胡利奧卸職,法比奧繼任鎮長一事就通過對話人稱謂的改變表現出來。精彩的對話藝術使得小說異彩紛呈,是對前述多面體結構的補充和具體化,使得多面體的每一面又呈現出凸凹不平的多面性,多角度的折射和反射使得多面體立體的小說撲朔迷離,耐人尋味,也使得小說具有了海明威所說的冰山一樣的宏偉、簡潔而蘊含豐富。
四、多面體的結構,謊言中的真實
在每一種新穎的形式背後都隐涵着作者對文學、對生活,乃至于對世界的理解。巴爾加斯·略薩也不例外,在《綠房子》的結構形式中寄寓了他對生活的理解和對文學的信念。社會生活本身并非首尾俱全、清晰明白、不蔓不枝的線性結構,人對生活的介入和了解不可能是因果分明的整體接受。
生活首先是以時間上的一個點、空間上的一個不完整的片段出現在人們面前,然後通過對其中人物的經曆、人物關系的逐步了解,對其中事件的尋根探源,生活才會把它的内部世界一點點展現于人們面前。"實際生活是流動的,不會停止,也無法度量,是一種混亂的狀态;每個曆史事件在混亂中與全部的曆史事件混合在一起,由此,每段曆史既無開頭也永遠沒有結尾"。
所以,人感受到的現實生活是零亂的、交叉的、頭緒紛繁的,人們感知的方式是探尋的、循序漸進的,因而,用線性結構講述多面體的生活是不妥當的,以全知全能叙述者的視角講述故事是違背生活真實的。普魯斯特說:"一些人執意認為小說要像電影鏡頭一般連貫地展現各種事情。
這種觀點是荒謬的。沒有任何東西比這樣一種電影鏡頭更遠離我們實際上所感知的東西。巴爾加斯·略薩顯然認同現代主義文學的真實觀。同樣,用線性思維思考多面體的生活不可避免地會曲解生活,因此作家的思維也應具有多面性,有深刻的思想和獨立的精神。因此,巴爾加斯·略薩繼阿斯圖裡亞斯和科塔薩爾之後,在文學創作中體現出沖破傳統線性思維的束縛,用多面性思維感知、思考和表達這個世界的傾向。他不主張簡單抄襲現實,而主張把現實肢解,然後加以誇張或濃縮,以更好地表現現實的多面性。
《綠房子》的多面體立體結構典型體現了作者對生活的這種認識,實踐了他的創作思想。在這裡,皮烏拉人、聖瑪麗亞·德·聶瓦鎮居民和山裡的印第安人同處于秘魯北部,生活在同一時代,生活卻有着天壤之别。在同一個時間的橫斷面上,作者立體地展示了不同生活圖景,組成了秘魯社會的一幅多彩的圖畫:玻璃球和小珠子換橡膠毛皮,印第安女孩被野蠻地從父母身邊拉走接受"文明"教育,土匪占島為王燒殺搶掠,鎮長走私橡膠謀取暴利⋯⋯文明與野蠻同時并存,所謂的文明與野蠻又成錯位。《綠房子》的多面體立體結構非常适宜表現秘魯當時波詭雲谲的現實生活。
《綠房子》精巧新穎的結構藝術折射出巴爾加斯·略薩的思想開放和蓬勃的創新追求。他在藝術上不斷創新,使得小說這種最契合于反映現代生活的文體煥發出勃勃生機。他善于推陳出新,每一部作品都開創新的藝術形式,從不因襲舊作。這種蓬勃的首創精神使他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
社會評論
《綠房子》揭露了當時秘魯存在的社會問題,控訴了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寄予了下層人民和貧苦婦女的深切同情,同時也充分展示了略薩對人類生存的認識與關懷。《綠房子》之所以長久不衰,除了迷人的結構寫實,還在于他作品中所體現的人性關懷。
略薩的作品中,最具革命性和典範性的不是眼花缭亂的結構變更,而是“小說需要介入”的政治和讓他憤怒不已的社會現實,正如略薩自己所言“文學就是火,它意味着叛逆和反抗,作家的價值就在于抗議、反駁和批判”。
——張瓊、黃德志
在《綠房子》中,略薩主要塑造了三種類型的人物群像:時代悲劇的體現者、受壓迫的女性、劍與十字架的統治者。如果說《綠房子》是一部描寫拉丁美洲的史詩的話,這些難逃命運戲弄的悲劇者則是最好的吟遊詩人:綠房子的第一代建造者安塞爾莫、原始叢林中土著首領胡姆、領水員聶威斯。這群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們是四處奔波的流浪者,是久覓不尋的永恒的失敗者,是連接沿海沙漠和原始森林的連通管,更是被時代命運流放的棄兒。
——易思
作者簡介
馬裡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擁有秘魯與西班牙雙重國籍的作家及詩人。創作小說、劇本、散文随筆、詩、文學評論、政論雜文,也曾導演舞台劇、電影和主持廣播電視節目及從政。詭谲瑰奇的小說技法與豐富多樣而深刻的内容為他帶來“結構寫實主義大師”的稱号。Mario是名字,Vargas(巴爾加斯)是父親的姓,Llosa(略薩)是母親的姓,分别代表Mario父親和母親的家族。
巴爾加斯·略薩于1936年3月28日生于秘魯南部亞雷基帕市,1953年進入秘魯國立聖馬爾科斯大學雙主修文學與法律,1957年入同校語言學研究所做研究生,1958年中旬以研究尼加拉瓜作家;詩人魯文·達裡奧的學位論文(《闡釋魯文·達裡奧的基礎》獲文學(語言學)學位,同年離開祖國秘魯移居歐洲,曾客居法國(主要在巴黎)、西班牙(主要在巴塞隆納)等國(後來他長期定居英國倫敦)。
巴爾加斯·略薩曾在英國劍橋大學擔任教職(1977年獲聘),也曾在英國倫敦大學(1967年和1969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75年)、美國哈佛大學(1992年)等校客座教職。n
略薩大部分作品中一個雷打不動的主題是反獨裁,極右(比如《城市與狗》和《酒吧長談》)和極左(比如《狂人瑪伊塔》)都是他批判的對象。略薩堅信,“小說需要介入政治”,這是讓小說變得尖銳而有力的重要武器之一。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