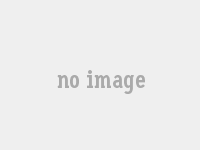疑問
《石頭記》伊始,娲皇氏煉石補天,單單一塊未用,棄于青埂峰下,此即整部《石頭記》生發之處。顯然,大荒頑石之所以源自娲皇氏者,關乎是書之宏旨自必甚巨也。曩古号為氏者,有所謂伏羲氏、有巢氏、燧人氏、神農氏。何以衆多男神不托,偏偏托于唯一之女神娲皇氏耶?
1、娲皇氏所煉之大荒頑石,男耶?女耶?
2、若曰大荒頑石為男,自必幻為神瑛侍者,绛珠仙子何所而來?
3、若曰大荒頑石為女,自必幻為绛珠仙子,神瑛侍者何所而來?
4、大荒頑石造劫曆世,何以由一僧一道陪同?
5、通靈寶玉曆世造劫,何以要予甄士隐一觀?
6、所謂甄氏士隐者,究系何方之神聖耶?
7、所謂一僧一道者,究系何方之妖魔耶?
8、所謂通靈寶玉者,究系何許之罕物耶?
9、所謂之大荒頑石者,作者耶?抑或作者之敵耶?
10、所謂之石頭一記,自述耶?抑或作者之他述耶?
上述之十大疑問,均系紅樓伊始之問題。顯然,倘若伊始即不懂,其後即自是更為不懂耳。由此可見,上之所問,自是紅論所首當闡述者。然而實況卻是,紅學大師不僅鮮有論及者,甚至一寫洋洋百十萬言,竟有始終未置一詞者。此種紅論,得無本末倒置,舍本逐末乎?
研究
俞平伯大約可說是新紅學(筆者将之定義為:認為紅樓一夢系曹寅後人所作的學派。)二号權威,但卻直到一九八六年,成名六十餘年之後,方始在其《舊時月色》一文中疑道:“又如大荒頑石與绛珠仙草、神瑛侍者的糾纏,觀空情戀,是二是一。始終不明。”六十年之後方始疑及于此,豈不有似乎長行千裡之後,複又疑及南轅是否北轍乎?
早在一九一九年,還在新紅學尚未萌芽之時,鄧狂言《紅樓夢釋真》:“托于女娲者……為孝莊(文皇後)寫照也。”世人所萬難接受者,整個紅學史上,于紅樓正文第一行,娲皇氏煉石補天一說,多少讀懂一點者,大約僅有鄧氏狂言一人耳。有人以紅學權威自居,實則就連正文首行之正解,尚亦讀之不懂耳。
紅樓一夢,說客極多,但卻無能得其頭緒,明其主幹,窺其宏旨,無能完全弄懂正文第一行者。紅樓傳世而今,垂二百五十年矣;紅學大師幾多于牛毛,諸般解數亦無不殆盡:所謂之紅學,何以仍是如此之糟耶?
紅樓一夢,就其隐意而言,當系朱明末系隐王,(約當1644??1700)由于身遭甲申之變,而又苦無回天之力,大約在一六八七年孝莊死後十餘年間,(為首)鑄就之隐書也。
紅樓一夢,主要是将孝莊當作滿清開國女皇,借以醜诋清國,謂其系由孝莊娘女,主要是由孝莊,以其下體之所換來。在寫到孝莊死亡時,即轉而預寫且一直寫到中州光複滿清複為後金止。
由于僅據成書年代,即不免為滿人揣知大意而遭焚禁,所以便被推遲到一七五二年左右方始(正式)付之傳世。為确保此書之得以傳世,主持是書傳世之隐者當曾施以脂批、托名以及分段傳世等輔助性手段。
所謂脂批,當即出于糊弄滿人之需要,着意杜撰之誤解,精心虛構之胡說也。
所謂托名,當即虛構曹寅有子雪芹論,(曹寅有孫及曾孫雪芹論,當亦根系于此)且托名為彼所作。
所謂分段傳世則可能是:先将首部甩而出之,神龍見首不見尾,其誰能識雌雄?待到首部風行之日,再将尾部甩而出之,即為看破底蘊而欲禁之,大不易也。
要而言之,《紅樓夢》者,朱明末系隐王本于中華而針對東胡之偉大“陰謀”耳。
一則因為對“陰謀”一無所知,而于紅樓不得其緒;
一則因為于紅樓不得其緒,而對“陰謀”一無所知:
兩扇大門一扇也打不開,所謂之紅學困境,實因于此。
更有甚者,身陷困境不自知,反把疑冢作正身,置諸多疑點不通于不顧,運用醒悟之後的俞平伯所謂煩瑣考證,僅憑那麼一點點傳聞,這是一種雞零狗碎并且錯而又錯自相矛盾的,很可能是源自一種騙局的傳聞,即硬斷紅樓一夢為曹寅之孫所作。(注意:作者曹雪芹論減去作者曹寅之孫論幾等于零。換言之,對于所謂“曹雪芹”本身,直到今天,幾乎仍然是一無所知。)
其邏輯簡直就象是,隻要抓住一根羊毛,即可得出結論,這東西絕對不是狼。
在“考定”所謂作者曹寅之孫論以後,再根據曹寅家世,根據曹錫遠從龍入關有功,根據出身成份論,硬将紅樓一夢朝非排滿方向附會,硬斷紅樓一夢無有排滿思想。
因為作者曹寅之孫論,意味着紅樓一夢無有排滿思想,意味着表面文字之下不可能有什麼隐意??滿清一朝,除了排滿之外,還有什麼東西必須深隐于表面文字之下???自然也就意味着紅樓本身之研究無甚必要,以緻紅學研究亦無甚必要矣。
因為紅樓一夢,正如孫靜庵所說,“無能窺其宏旨者”,紅學研究的确有其必要;可是按之作者曹寅之孫論,紅樓本身之研究卻既無必要又無從着手:就在這種必須研究但又無須研究而且無從研究的困境之中,形成了一個置紅樓本身于不顧,一味大搞其曹學,一味大走其紅外線的,以曹學代替紅學的怪胎??新紅學。
由于以曹代紅,新紅學除了空殼性的,顯然不通的自傳家史論及其三五個變種之外,其實什麼也沒有。
時至今日,新紅一派之于紅樓宏旨,實已不知究應何等樣說方妙矣。自傳說?家史說?社會說?情場忏悔論?意在戒淫論?谶緯命相論?從索隐派那兒借來的雍正奪嫡論?霍氏姐弟的曹雪芹毒死雍正皇帝論?尤其是紅研所的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論?……叫我看,即論者自身亦不甚相信也。
八十年前,胡适《紅樓夢考證》,說什麼要搞“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
八十年後,鄙意則以為,胡适不僅于紅樓無甚研究,而且很可能,即畢其一生亦未能通讀紅樓一過。(從胡适論紅全編來看,在發表《紅樓夢考證》之前,胡似無研究紅樓本身之時間。就胡适觀點而言,一部不僅沒有寫完而且寫得并不怎麼好的坐吃山空性自傳,亦無甚研究之必要。)于是便有一問題,胡于紅樓無甚研究,又豈能創立新紅一派,并在論戰中“戰勝”研紅二十餘年之蔡元培耶?
其實,胡适所謂“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隻不過以一種很可能源自騙局的傳聞為根據,将紅樓一夢斷為曹寅之孫所作,将曹學納入紅學範疇,從而形成了一條,幾乎無須涉及超難度的紅樓一夢,隻要大談普通難度的曹學,即可成為紅學專家的捷徑,并且以自身為榜樣,創造了一個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紅學的新紅學而已。
統而言之,所謂新紅學,其實隻不過一場夢外之夢罷了。
鄙人不會作詩,又好附庸風雅,無奈之餘,便隻好半偷半哄道:
夢外之夢樓外樓,紅外歌舞幾時休?
因為新紅學家必不以鄙說為然,所以鄙人先鄭重請教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大荒頑石究竟是男是女?
大荒頑石究竟是男是女:就漢學而言,因為此一問題倘能完美解答,整部紅樓便業已相當完美地解答完畢,而紅樓一夢又可謂漢學之第一大難,所以可以說,此亦漢學之第一大難。
大荒頑石究竟是男是女:就紅樓而言,此一問題相當于千裡長行第一步。顯然,倘若就連第一步也還不能解答,别的自然也就不用說了。
大荒頑石究竟是男是女:新紅學家能否解答耶?顯然,新紅學家隻要有一個人能夠作出解答,俞平伯即不緻有所謂“是二是一,始終不明”之歎。
大荒頑石究竟是男是女:如上所述,新紅學家必然誰也不能解答。既然就連千裡長行第一步也還不能解答,恐怕應該謙虛一點,誠實一點……
紅樓一夢,其第一大要,在排滿二字。
由排滿二字所決定,其成書過程和傳世手段必然甚為詭異。這就意味着,有關是書之作者、成因及來路的,各式各樣而又雞零狗碎錯漏百出的零星記載,很可能是源自一種騙局。倘就新紅學家據以證明作者曹寅之孫論的所謂論據而言,就沒有哪一條是言之鑿鑿确切可信的,就沒有哪一條不是錯而又錯自相矛盾的。而這又進一步意味着,研究紅樓一夢的可靠材料,大體隻有紅樓一夢本身。
由排滿二字所決定,紅樓一夢的表達方式必然亦甚為詭異。至少可以相信,必系滿人所幾乎不可弄懂者。滿人既幾乎不可弄懂,他人自亦幾乎不可弄懂矣。
雖說幾乎不可弄懂,但因為作者創寫此書不可能不希望被人弄懂,所以弄懂紅樓一夢并非不可能。
鄙人琢磨紅樓十五年,自信至少弄懂紅樓正文第一行。
萬勿小看第一行,因為此語系借娲皇氏隐示紅樓主角,而可能與娲皇氏相關者,卻僅有孝莊、呂後、武則天數人而已??倘系其他任何一個男人,或女而不皇,皇而并非“始皇”者,當決無托生于娲皇氏之理??所以僅此第一行,即已于作者身世、成書年代、頭緒結構以及手法宏旨等項,決定甚多矣。
因此可曰:不懂紅樓正文第一行,紅學研究即不得其門而入。
倘将弄懂紅樓一夢比做從一座迷宮走将出來,娲皇氏煉石補天即為此一迷宮之入口。紅樓說客雖多,但卻就連鄧氏狂言亦未能意識到,此乃迷宮之入口耳。迷宮入口尚且不知,又何言從彼端走将出來?又何言弄懂紅樓一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