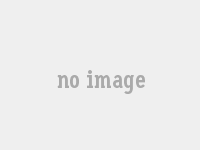作者簡介
蒲松齡(1640年6月5日—1715年2月25日),字留仙,又字劍臣,号柳泉居士,世稱聊齋先生,自稱異史氏。淄川(今山東省淄博市淄川區)城外蒲家莊人。清代著名的小說家、文學家。
原文
陵陽朱爾旦,字小明。性豪放,然素鈍,學雖笃,尚未知名。一日,文社衆飲。或戲之雲:“君有豪名,能深夜赴十王殿,負得左廊判官來,衆當醵作筵。”蓋陵陽有十王殿,神鬼皆以木雕,妝飾如生。東庑有立判,綠面赤須,貌尤獰惡。或夜聞兩廊拷訊聲。入者,毛皆森豎。故衆以此難朱。朱笑起,徑去。居無何,問外大呼曰:“我請髯宗師至矣!”衆皆起。俄負判入,置幾上,奉觞,酹之三。衆睹之,瑟縮不安于座,仍請負去。朱又把酒灌地,祝曰:“門生狂率不文,大宗師諒不為怪。荒舍匪遙,合乘興來覓飲,幸勿為畛畦。”乃負之去。
次日,衆果招飲。抵暮,半醉而歸,興未闌,挑燈獨酌。忽有人奉簾入,視之,則判官也。朱起曰:“意吾殆将死矣!前夕冒渎,今來加斧耶?”判啟濃髯,微笑曰:“非也。昨蒙高義相訂,夜偶暇,敬踐達人之約。”朱大悅,牽衣促坐,自起滌器火。判曰:“天道溫和,可以冷飲。”朱如命,置瓶案上,奔告家人洽肴果。
妻聞,大駭,戒勿出。朱不聽,立俟治具以出。易盞交酬,始詢姓氏。曰:“我陸姓,無名字。”與談古典,應答如響。問:“知制藝否?”曰:“妍亦頗辨之。陰司誦讀,與陽世略同。”陸豪飲,一舉十觥。朱因竟日飲,遂不覺玉山傾頹,伏幾醺睡。比醒,則殘燭昏黃,鬼客已去。
自是三兩日辄一來,情益洽,時抵足卧。朱獻窗稿,陸辄紅勒之,都言不佳。一夜,朱醉,先寝,陸猶自酌。忽醉夢中,覺髒腹微病;醒而視之,則陸危坐床前,破腔出腸胃,條條整理。愕曰,“夙無仇怨,何以見殺?”陸笑雲:“勿懼,我為君易慧心耳。”從容納腸己,複合之,末以裹足布束朱腰。作用畢,視榻上亦無血迹。腹間覺少麻木。見陸置肉塊幾上。問之,曰:“此君心也。作文不快,知君之毛竅塞耳。适在冥間,于千萬心中,揀得佳者一枚,為君易之,留此以補阙數。”
乃起,掩扉去。天明解視,則創縫已合,有線而赤者存焉。自是文思大進,過眼不忘。數日,又出文示陸。陸曰:“可矣。但君福薄,不能大顯貴,鄉、科而已。”問:“何時?”曰:“今歲必魁。”未幾,科試冠軍,秋闱果中經元。同社生素揶揄之;及見闱墨,相視而驚,細詢始知其異。共求朱先容,願納交陸。陸諾之。衆大設以待之。更初,陸至,赤髯生動,目炯炯如電。衆茫乎無色,齒欲相擊;漸引去。
朱乃攜陸歸飲,既醺,朱曰:“湔腸伐胃,受賜已多。尚有一事欲相煩,不知可否?”陸便請命。朱曰:“心腸可易,面目想亦可更。山荊,予結發人,下體頗亦不惡,但頭面不甚佳麗。尚欲煩君刀斧,如何?”陸笑曰:“諾,容徐圖之。”過數日,半夜來叩關。朱急起延入。燭之,見襟裹一物。诘之,曰:“君曩所囑,向艱物色。适得一美人首,敬報君命。”朱撥視,頸血猶濕。陸立促急入,勿驚禽犬。朱慮門戶夜扃。
陸至,一手推扉,扉自辟。引至卧室,見夫人側身眠。陸以頭授朱抱之;自于靴中出白刃如匕首,按夫人項,着力如切腐狀,迎刃而解,首落枕畔;急于生懷,取美人首合項上,詳審端正,而後按捺。已而移枕塞肩際,命朱瘗首靜所,乃去。朱妻醒,覺頸間微麻,面頰甲錯;搓之,得血片,甚駭。呼婢汲盥;婢見面血狼借,驚絕。濯之,盆水盡赤。舉首則面目全非,又駭極。夫人引鏡自照,錯愕不能自解。朱入告之;因反複細視,則長眉掩鬓,笑靥承顴,畫中人也。解領驗之,有紅線一周,上下肉色,判然而異。
先是,吳侍禦有女甚美,未嫁而喪二夫,故十九猶未蘸也。元遊十王殿,時遊人甚雜,内有無賴賊窺而豔之,遂陰訪居裡,乘夜梯入,穴寝門,殺一婢于床下,逼女與淫;女力拒聲喊,賊怒,亦殺之。吳夫人微聞鬧聲,呼婢往視,見屍駭絕。舉家盡起,停屍堂上,置首項側,一門啼号,紛騰終夜。诘旦啟衾,則身在而失其首。遍撻侍女,謂所守不恪,緻葬犬腹。侍禦告郡。郡嚴限捕賊,三月而罪人弗得。漸有以朱家換頭之異聞吳公者。
吳疑之,遣媪探諸其家;入見夫人,駭走以告吳公公視女屍故存,驚疑無以自決。猜朱以左道殺女,往诘朱。朱曰:“室人夢易其首,實不解其何故;謂仆殺之,則冤也。”吳不信,訟之。收家人鞠之,一如朱言。郡守不能決。朱歸,求計于陸。陸曰:“不難,當使伊女自言之。”吳夜夢女曰:“兒為蘇溪楊大年所賊,無與朱孝廉。彼不豔于其妻,陸判官取兒頭與之易之,是兒身死而頭生也。願勿相仇。”醒告夫人,所夢同。乃言于官。
問之,果有楊大年;執而械之,遂伏其罪。吳乃詣朱,請見夫人,由此為翁婿。乃以朱妻首合女屍而葬焉。朱三入禮闱,皆以場規被放。于是灰心仕進,積三十年。一夕,陸告曰:“君壽不永矣。”問其期,對以五日。“能相救否?”曰:“惟天所命,人何能私?且自達人觀之,生死一耳,何必生之為樂,死之為悲?”
朱以為然。即治衣衾棺椁;既竟,盛服而沒。翌日,夫人方扶柩哭,朱忽冉冉自外至。夫人懼。朱曰:“我誠鬼,不異生時。慮爾寡母孤兒,殊戀戀耳。”夫人大恸,涕垂膺;朱依依慰解之。夫人曰:“古有還魂之說,君既有靈,何不再生?”朱曰:“天數不可違也。”問,“在陰司作何務?”曰:“陸判薦我督案務,授有官爵,亦無所苦。”
夫人欲再語,朱曰:“陸公與我同來,可設酒馔。”趨而出。夫人依言營備。但聞室中笑飲,亮氣高聲,宛若生前。半夜窺之,然己逝。自是三數日辄一來,時而留宿缱绻,家中事就便經紀。子玮方五歲,來辄捉抱;至七八歲,則燈下教讀。子亦慧,九歲能文,十五入邑庠,竟不知無父也。從此來漸疏,日月至焉而已。又一夕來,謂夫人曰:“今與卿永訣矣。”問:“何往?”曰:“承帝命為太華卿,行将遠赴,事煩途隔,故不能來。”母子持之哭,曰:“勿爾!兒已成立,家計尚可存活,豈有百歲不拆之蠻鳳耶!”顧子曰:“好為人,勿堕父業。十年後一相見耳。”徑出門去,于是遂絕。
後玮二十五舉進士,官行人。奉命祭西嶽,道經華陰,忽有輿從羽葆,馳沖鹵簿。訝之。審視車中人,其父也。下車哭伏道左。父停輿曰:“官聲好,我目瞑矣。”玮伏不起;朱促輿行,火馳不顧。去數步,回望,解佩刀遣人持贈。遙語曰:“佩之當貴。”玮欲追從,見輿馬人從,飄忽若風,瞬息不見。痛恨良久;抽刀視之,制極精工,镌字一行,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玮後官至司馬。生五子,曰沉,曰潛,曰沕,曰渾,曰深。一夕,夢父曰:“佩刀宜贈渾也。”從之。渾仕為總憲,有政聲。
異史氏曰:“斷鶴續凫,矯作者妄;移花接木,創始者奇;而況加鑿削于肝腸,施刀錐于頸項者哉!陸公者,可謂皮裹妍骨矣。明季至今,為歲不遠,陵陽陸公猶存乎?尚有靈焉否也?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注釋
陵陽:舊縣名。今為陵陽鎮,屬安徽省青陽縣。
鈍:遲鈍,愚笨。
笃:專心、勤奮。
文社:科舉時代,秀才們講學作文的結社。
十王殿:廟宇名。十王,中國佛教所傳十個主管地獄的閻王之總稱,也稱“十殿閻君”,略稱“十王”。後道教也沿用此稱。
判官:官名。唐始設。為節度、觀察、防禦諸使的僚屬。此指迷信傳說中為閻王掌簿冊的佐吏。
醵(jù據):湊錢飲酒。
東庑(wú武):即東廊。庑,殿堂下周圍的走廊或廊屋。此指廊屋。
毛皆森豎:因恐懼而毛發都聳立起來。森,高聳。
宗師:舊稱受人尊崇堪為師表的人。明、清稱學使為“宗師”。朱爾旦負陸判至“文社”故用以戲稱。
酹(lèi類):以酒澆地,祭祀鬼神。
瑟縮:因恐懼而抖戰、蜷縮。
門生:自唐至明,科舉制度中,貢舉之士以主考官員為座主,而自稱門生。此處既已稱陸判為”宗師”,而“宗師”(即學使)又為各省鄉試的主考官,朱因以自稱。狂率不文:狂妄輕率,不懂禮儀。文,禮法。
合:應,合當。
勿為畛(zhěn診)畦(qí齊):意謂不要為人鬼異域所限。畛畦,田間小路,引申為界限、隔閡。
意:自料。
斧:古代殺人的刑具。斧謂刀刃,謂砧闆;“加斧”,指加以死罪。
高義:猶高誼、盛情。相訂:猶相約。訂,定,約定。
達人:曠達之人。
治具:置辦酒肴。具,餐具,代指酒肴。
古典:古代的典籍。此指具有典範性的古代名着。
制藝:制舉應試文章,指八股文。詳前《嬌娜》注。
玉山傾頹:形容酒醉。《世說新語·容止》:“嵇叔夜之為人也,岩岩苫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玉山,形容體态、儀表美好。
窗稿:指平時習作的文稿。讀書人慣常在窗下寫文章,故稱。
紅勒:用朱筆删削、批改,《夢溪筆談·人事》載:北宋嘉年間,士人劉幾“累為國學第一,驟為怪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指歐陽修)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紅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幾也。”
作用:施治,整治。用,治。
鄉、科:鄉試、科試的省詞。詳《葉生》注。
魁:奪魁,考取第一名。即下文所謂“科試冠軍”、“秋闱果中經元”。
秋闱:指鄉試。舊稱試院為“闱”,而鄉試在秋間舉行,因稱。經元:也稱經魁。明清科舉考試,分五經取士。鄉試及會試前五名,各為一經中的第一名。
闱墨:清代于每屆鄉試、會試之後,由主考宮選取中式試卷,編輯成書,叫做“闱墨”。
先容:事先為人作介紹。
湔(jiān煎)腸伐胃:洗腸剖胃。《五代史·周書·王仁裕傳》:王仁裕少不知學,二十五歲方思學習,“一夕,夢剖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資性絕高。”
山荊:對人稱謂自己妻室的謙詞。說本《太平禦覽》七一八引《列女傳》:“梁鴻妻孟光,荊钗布裙。”
結發人:元配妻子。古時男子二十歲束發加冠,女子十五歲盤發貫笄(簪),即為成年。因此習稱元配妻子為“結發人”。《玉台新詠·留别妻》:“結發為夫妻,恩愛兩不疑。”
甲錯:鱗甲錯雜。此指面頰血污結痂,像魚鱗似的。
笑靥(yè夜)承顴(quán權):謂女子笑時口旁現出兩個酒窩。靥,口旁窩,俗稱酒窩。顴,顴骨。酒窩在顴骨的下面,故雲“承”。
侍禦:官名。禦史的别稱。明、清屬都察院,職稱有左右都禦史、左右副都禦史、左右佥都禦史、監察禦史之别。
醮(jiào較):斟酒飲對方;古時婚禮中的一種儀節。《禮記·昏義》:“父親醮子而命之迎。”本指男女婚禮,元明以後則專指女子再嫁。
陰訪:暗中查訪。
诘旦:诘朝,第二天早晨。
不恪(kè客):不慎。恪,謹慎,恭敬。
郡:此指郡衙。明、清兩代指知州、知府一類地方官的衙署。
左道:邪道,邪術。
鞫(jú局):審訊。
不能決:此據鑄雪齋抄本,底本“能”字殘缺。
伊:底本殘缺。此據鑄雪齋抄本。
賦:殺害。
無與朱孝廉:與朱孝廉無關。孝廉,明,清指舉人。詳前《畫壁》注。
禮闱:即會試。會試于鄉試後第二年春季在禮部舉行,故又稱“禮闱”。
以場規被放:由于違犯考場規則而被逐出場外或不予錄取。科舉考場對參加考試的人規定一些條文,諸如挾帶文書入場,或親族任考官而不加回避等,均為違犯“場規”。而考卷違式,如題目寫錯,污損卷紙,擡頭錯誤,不避聖諱等,也往往被取消考試資格。此處指後者。放,驅逐。
膺:胸。
天數:猶天命。
督案務:監理案犢方面的事務。督,察視。案,案牍,官府文書。
(yǎo咬)然:深遠難見的樣子。
經紀:料理。
邑庠:縣學。詳前《葉生》注。
日月至焉:偶然來一次。語出《論語·雍也》。
太華卿:華山山神。太華,即西嶽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南。因其西有少華山,故又稱”太華”。
行人:官名。明代設有行人司,置司正及左右司副,下有行人若幹,以進士充任。行人職掌捧節奉使;凡頒沼、冊封、撫谕、征聘及祭祀山川神祗,都差行人。
華陰:縣名。今屬陝西省。
輿從羽葆:車馬儀仗。輿從,車馬前後的侍從;羽葆,儀仗名,以鳥羽為裝飾。《禮記·雜記》:“匠人執羽葆禦柩。”孔穎達疏:“羽葆者,以鳥羽注于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
鹵簿:秦、漢時皇帝輿駕行幸時的儀仗隊。漢以後王公大臣均置鹵簿。因亦泛指官員儀仗。鹵,大型甲盾。甲盾的排列,有明确規定,且着之簿籍,因稱“鹵簿”。
聲:聲譽。下文“政聲”之“聲”,義同。
镌(juān捐):刻。
“膽欲大”二句:意謂任事要果決,而思慮要周密;智謀要圓通,而行為要方正。語見《舊唐書·孫思邈傳》。
司馬:官名。古為管領軍隊官員的稱謂。漢武帝置大司馬,為全國軍政首腦,明、清時期用為兵部尚書的别稱,侍郎稱少司馬。此或指兵部尚書、侍郎一類官員。
總憲:明、清為都察院左都禦史的别稱。
“斷鶴”二句:意謂如因鶴腿長而截之使短,因凫(野鴨)腿短而續之使長,如此矯情而作者是妄為。《莊子·骈拇》:“凫胫雖短,續之則憂;鶴胫雖長,斷之則悲。”妄,謬,荒謬。
移花接木:謂将一種花木嫁接于另一種花木之上。喻暗中巧施手段改造人的形體。
媸(chī吃)皮裹妍骨:謂相貌醜陋而内心美好。媸,醜陋。媸皮,醜陋的相貌。妍,美。妍骨,美好的骨肉,此謂美好的品行。
明季:明代末年。
為歲:猶為時。歲,指時間。
為之執鞭:為其趕車,做仆役。表示對人極度欽佩。《史記·管晏列傳》:“假令晏子而在,餘雖為之執鞭、所忻墓焉。”
白話譯文
陵陽人朱爾旦,字小明,性情豪放。但他生性遲鈍,讀書雖然很勤苦,卻一直沒有成名。
一天,朱爾旦跟幾個文友一塊喝酒。有人跟他開玩笑說:“你以豪放聞名,如能在深夜去十王殿,把左廊下那個判官背了來,我們大家就做東請你喝酒。”原來,陵陽有座十王殿,殿裡供奉着的鬼神像都是木頭雕成的,妝飾得栩栩如生。在大殿東廊裡有個站着的判官,綠色臉膛,紅色胡須,相貌尤其猙獰兇惡。有人曾聽見夜間兩廊裡傳出審訊拷打聲。凡進過殿的人,無不毛骨悚然。所以大家提出這個要求來為難朱爾旦。朱聽了,一笑而起,徑自離席而去。
過了不久,隻聽門外大叫:“我把大胡子宗師請來了!”大家剛站起來,朱爾旦背着判官走了進來。他把判官放在桌子上,端起酒杯來連敬了三杯。衆人看見判官的模樣,一個個在座上驚恐不安,忙請朱爾旦再背回去。朱又舉起酒杯,把酒祭奠在地上,禱告說:“學生粗魯無禮,諒大宗師不會見怪!我的家距此不遠,請您什麼時候有興緻了去喝兩杯,千萬不要拘于人神有别而見外!”說完,仍将判官背了回去。
第二天,大家果然請朱爾旦喝酒。一直喝到天黑,朱爾旦喝得醉醺醺地回到家中。酒瘾沒過,他又掌上燈,一個人自斟自飲。忽然,有個人一掀門簾走了進來。朱爾旦擡頭一看,竟是那個判官!他忙站起身說:“咦!看來我要死了!昨晚冒犯了您,今晚是來要我命的吧?”判官大胡子一動一動的,微笑着說:“不是的。昨晚承蒙你慷慨相邀,今晚正好有空,所以特來赴你這位通達之人的約會。”朱爾旦大喜,拉着判官的衣服請他快坐下,自己起來刷洗酒具,又燒上火要溫酒。
判官說:“天氣暖和,我們涼喝吧。”朱爾旦聽從了,把酒瓶放在桌子上,跑了去告訴家人置辦菜肴、水果。他妻子知道後,大吃一驚,勸阻他躲在屋裡别出去了。朱爾旦不聽,立等她準備好菜肴,然後端了過去,又換了酒杯,兩個人便對飲起來。朱爾旦詢問判官的姓名。判官說:“我姓陸,沒有名字。”朱爾旦跟他談論起古典學問,判官對答如流。
朱爾旦又問他:“懂得現時的八股文嗎?”判官說:“好壞還能分得出來。陰間裡讀書作文跟人世差不多。”陸判官酒量極大,一連喝了十大杯。朱爾旦因為已喝了一整天,不覺大醉,趴在桌子上沉沉睡去。等到一覺醒來,隻見殘燭昏黃,鬼客已經走了。
從此後,陸判官兩三天就來一次,兩人更加融洽,經常同床而眠。朱爾旦把自己的文章習作呈給陸判官看,陸判官拿起紅筆批改一番,都說不好。一夜,兩人喝過酒後。朱爾旦醉了,自己先去睡下了,陸判官還在自飲。朱爾旦睡夢中,忽覺髒腑有點疼痛,醒了一看,隻見陸判官端坐床前,已經給他剖開肚子,掏出腸子來,正在一根一根地理着。
朱爾旦驚愕地說:“我們并無仇怨,為什麼要殺我呢?”陸判官笑着說:“你别害怕,我要為你換顆聰明的心。”說完,不緊不慢地把腸子理好,放進朱爾旦的肚子裡,把刀口合上,最後用裹腳布把腰纏起來。一切完畢,見床上一點血迹也沒有,朱爾旦隻覺得肚子上稍微有些發麻。又見陸判官把一團肉塊放到桌子上,朱爾旦問是什麼東西,陸判官說:“這就是你原來的那顆心。你文思不敏捷,我知道是因為你心竅被堵塞的緣故。剛才我在陰間裡,從千萬顆心中選了最好的一顆,替你換上了,留下這個補足缺數吧。”說完,便起身掩上房門走了。
天明後,朱爾旦解開帶子一看,傷口已好了,隻在肚子上留下了一條紅線。從此後,他文思大進,文章過目不忘。過了幾天,他再拿自己的文章給陸判官看,陸判官說:“可以了。不過你福氣薄,不能做大官,頂多中個舉人而已。”朱爾旦問:“什麼時候考中?”“今年必考第一!”陸判官回答。
不久,朱爾旦以頭名考中秀才,秋天科考時又中了頭名舉人。他的同窗好友一向瞧不起他,等見了他的考試文章,不禁面面相觑,大為驚訝。仔細詢問朱爾旦,才知道是陸判官給他換了慧心的結果。衆人便請朱爾旦把陸判官給大家介紹介紹,都想結交他。陸判官痛快地答應了。衆人便大擺酒席。等着招待陸判官。
到了一更時分,陸判宮來了。隻見他紅色的大胡子飄動着,炯炯的目光像閃電一樣,直透人心。衆人臉上茫然失色,牙齒不禁格格作響。過了不久便一個跟着一個地離席逃走了。朱爾旦便請陸判官到自己家去喝。二人喝得醉醺醺的時候,朱爾旦說:“你替我洗腸換心,我受你的恩惠也不少了!我還有件事想麻煩你,不知可以嗎?”陸判官請他說。
朱爾旦說:“心腸既能換,想來面目也可以換了。我的結發妻子身子倒還不壞,隻是眉眼不太漂亮,還想麻煩你動動刀斧,怎麼樣?”陸判官笑着說:“好吧,讓我慢慢想辦法。”
過了幾天,陸判官半夜來敲門。朱爾旦急忙起床請他進來。點上蠟燭一照,見陸判官用衣襟包着個東西,朱爾旦問是什麼。陸判官說:“你上次囑咐我的事,一直不好物色。剛才恰巧得到一個美人頭,特來履行諾言來了!”朱爾旦撥開他的衣襟一看,見那腦袋脖子上的血還是濕的。陸判官催促快去卧室,不要驚動雞犬。
朱爾旦擔心妻子卧室的門晚上闩上了。陸判官一到,伸出一隻手一推,門就開了。進了卧室,見朱爾旦的妻子側身熟睡在床上。陸判官把那顆腦袋交給朱爾旦抱着,自己從靴子中摸出把匕首,一手按住朱妻的脖子,另一隻手像切豆腐一樣用力一割,朱妻的腦袋就滾落在枕頭一邊了。陸判官急忙從朱爾旦懷中取過那顆美人頭,安在朱妻脖子上,又仔細看了看是否周正,用力按了按,然後移過枕頭,塞到朱妻腦袋下面。一切完畢,命朱爾旦把割下的腦袋埋到一處無人的地方,自己才離去了。
朱妻第二天醒來,覺得脖子上微微發麻,臉上幹巴巴的。用手一搓,有些血片,大吃一驚,忙喊丫鬟取水洗臉。丫鬟端水進來,見她一臉血污,驚駭萬分。朱妻洗了臉,一盆水全變成了紅色。她一擡頭,丫鬟猛然見她面目全非,更加吃驚。朱妻自己取過鏡子來照了照,驚愕萬分,百思不得其解。朱爾旦進來後,告訴了妻子陸判官給換頭的經過,又反複打量妻子,見她秀眉彎彎,腮兩邊一對酒窩,真像是畫上的美人。解開衣領一看,脖子上隻留下了一圈紅線,紅線上下的皮膚顔色截然不同。
在此以前,吳侍禦有個女兒,非常漂亮。先後兩次訂親,但都沒過門丈夫就死了,所以十九歲了還沒嫁人。上元節時,吳女去逛十王殿,當時遊人又多又雜,内中有個無賴窺視到她容貌豔麗,便暗暗訪查到她的家,夜晚用梯子翻牆進院,從她卧室的門上打個洞鑽進去,先把一個丫鬟殺死在床下,然後威逼要奸淫吳女。
吳女奮力抗拒,大聲呼救,無賴發怒,一刀把她腦袋砍了下來。吳夫人隐約聽見女兒卧室裡有動靜,喊丫鬟去察看,丫鬟一見房間裡的屍體,差點吓死過去。全家人都起來了,把屍體停放在堂屋裡,把吳女的頭放在她的脖子一側。一家人号啕大哭,亂了一整夜。第二天黎明,吳夫人掀開女兒屍體上的被子一看,身子在,頭卻不見了。氣得她将看守屍體的侍女挨個痛打了一頓,還以為是她們看守不嚴,被狗叼去吃了。吳侍禦立即把女兒被殺的事告訴了郡府。郡守嚴令限期緝捕兇手,可三個月過去了,兇手仍沒抓到。
不久,朱爾旦的妻子換了腦袋的奇異消息,漸漸傳入吳侍禦的耳朵裡。他起了疑團,派了一個老媽子借故去朱家探看。老媽子一見朱夫人的模樣,立刻驚駭地跑回來告訴了吳公。吳公見女兒屍體還在,心中驚疑不定,猜測可能是朱爾旦用邪術殺了女兒,便親自去盤問朱爾旦。朱說:“我妻子在睡夢中被換了腦袋,實在不知是怎麼回事!說我殺了你女兒,真是冤枉!”吳公不信,告了郡府。郡守又把朱爾旦的家人抓了去審訊,結果和朱說的一樣,郡守也判斷不清。
朱爾旦回家後,向陸判官求計。陸判官說:“這不難,我讓他女兒自己說清楚。”到了夜晚,吳侍禦夢見女兒跟自己說:“女兒是被蘇溪的楊大年殺害的,與朱舉人沒有關系。朱舉人嫌妻子長得醜,所以陸判官把女兒的頭給朱妻換上了。現在女兒雖然死了,但腦袋還活着,願我們家不要跟朱舉人為仇。”吳侍禦醒後,忙把夢告訴了夫人,夫人也做了個同樣的夢。于是又告訴了郡府,郡守一問,果然有個楊大年。立即抓了來一拷問,楊大年供認了罪行。吳侍禦便去拜訪朱爾旦,請求見一見朱夫人。又認了朱夫人為女兒,和朱爾旦結成了翁婿。于是把朱夫人的腦袋安在吳女屍體上埋葬了。
後來,朱爾旦又三次進京考進士,都因為違犯了考場規矩而被黜名。他由此灰心喪氣,不再想做官。過了三十年,有一晚,陸判官告訴朱爾旦說:“你的壽命快到頭了。”朱爾旦詢問死的日期,陸判官回答說五天後。“能挽救嗎?”陸判官說:“生死全由天定,人怎能改變呢?況且在通達人看來,生和死是一樣的,何必活着就認為是快樂,而死了就覺得悲哀呢?”朱爾旦聽了,覺得很對,便置辦起壽衣棺材。五天後,他穿着盛裝去世了。
第二天,朱夫人正在扶着靈柩痛哭,朱爾旦忽然飄飄忽忽地從外面走來了。朱夫人害怕,朱爾旦說:“我确實是鬼,但和活着時沒什麼兩樣。我挂念着你們孤兒寡母,實在是戀戀不舍啊!”夫人聽了,号啕大哭,淚水一直流到胸前。朱爾旦愛撫地勸慰着妻子,夫人說:“古時有還魂的說法,你既然有靈,為什麼不再托生呢?”
朱爾旦說:“天數怎能違背呢?”妻子又問:“你在陰間幹些什麼?”朱爾旦回答說:“陸判官推薦我掌管文書,還封了官爵,也沒什麼苦處。”妻子還想再問,朱爾旦說:“陸公跟我一塊來了,快點準備酒菜吧。”說完便出去了。朱夫人立即按丈夫吩咐的去準備。一會兒,便聽見陸判官和朱爾旦二人在室内飲酒歡笑,高腔大嗓,宛如生前。到了半夜,再往屋裡一看,二人已都不見了。
從此後,朱爾旦幾天就來一次,有時就在家裡和妻子同宿,順便料理料理家務事。當時,他的兒子朱玮才五歲。朱爾旦來了後,就抱着他。朱玮長到七八歲,朱爾旦又在燈下教他讀書。兒子很聰明,九歲能寫文章,十五歲考進了縣學,還依然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早已去世多年。但此後,朱爾旦來的次數漸漸少了,有時個把月才來一次。
又一天晚上,朱爾旦來了,跟妻子說:“現在要和你永别了!”妻子問:“你要去哪裡?”朱回答說:“承蒙上帝任命我為太華卿,馬上就要去遠方赴任。公務繁忙,路途又遙遠,所以不能再來了。”妻子和兒子聽了,抱着他痛哭。朱爾旦安慰說:“不要這樣!兒子已長大成人,家境也還過得去,世上哪有百年不散的夫妻?”又看着兒子囑咐說:“好好做人,不要荒廢了父親教給的學業。十年後還能見面。”說完,徑直出門走了。從此再沒來過。
後來,朱玮二十五歲時考中了進士,做了行人官,奉皇帝令去祭祀西嶽華山。路過華陰的時候,忽然有支打着儀仗的人馬,急速沖來,也不回避朱玮的隊伍。朱玮十分驚異,細看對方車中坐着的人,竟是父親!朱玮忙跳下馬來,跪在路邊痛哭。父親停下車子,說:“你做官的聲譽很好,我可以閉目了。”
朱玮哭着跪在地上不起來。朱爾旦不顧,催促車輛飛速馳去。剛走了不幾步,又回頭望了望,解下身上的佩刀,派個人回來送給朱玮,遠遠地喊道:“佩上這把刀,可以富貴!”朱玮要追着跟去,隻見父親的車馬從人,飄飄忽忽地像風一樣,瞬間便消失不見了。朱玮怅痛了很久,無可奈何。抽出父親送給的刀看了看,制作極其精細,刀上刻着一行字:“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
後來,朱玮做官一直做到司馬。生了五個兒子,依次是:朱沉、朱潛、朱沕、朱渾、朱深。有一晚,朱玮夢見父親告訴自己說:“佩刀應贈給朱渾。”朱玮聽從了。後來朱渾官至總憲,很有政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