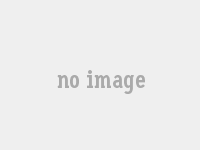叙述文學
理論家在描述一個文本的叙事結構時,會涉及結構元素,例如:
介紹——故事中的角色及其環境是如何塑造的;合聲——以旁觀者的語氣描述事态或指示适當的情緒反應;尾聲——終止于叙事結尾并做終結注釋。古希臘哲學家亞裡士多德和柏拉圖最早提出叙事結構的概念,在二十世紀中晚期,再次引起關注。羅蘭·巴特(RolandBarthes)、弗拉迪米爾·普洛普(VladimirPropp)、約瑟夫·坎貝爾(JosephCampbell)和諾思洛普·弗萊(NorthropFrye)試圖論證人類叙事的普遍性,發現其中深層的基本元素。
當後結構主義理論家米歇爾·福柯(MichelFoucault)、雅克·德裡達(JacquesDerrida)等人宣稱這種深層結構在邏輯上根本不可能存在時,關于叙事結構的争論再次浮出水面。諾思洛普·弗萊(NorthropFrye)在其着作《批評的剖析》中,将叙事結構分為春、夏、秋、冬四種,他稱之為“原型”。
冬對應于反烏托邦,例如喬治·奧威爾(GeorgeOrwell)的《一九八四》和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Huxley)的《美麗新世界》。春的原型對應于喜劇,也就是說,那些會将糟糕的局面導向快樂結尾的故事。如莎士比亞的《第十二夜》。夏的原型對應于烏托邦幻想,如但丁《神曲》中的天堂。秋的原型對應于悲劇,其中理想的情形走向災難。例如《哈姆雷特》、《奧塞羅》、《李爾王》以及近期好萊塢的《秋天的傳說》都屬于這種情況。
叙述電影
電影是一種叙事為主的藝術,其叙事方法雖千奇百怪、變化多端,但其結構模式可歸納為幾種類型。結構指作品内容的組織、安排、構造,如詞組結構、句型結構、段落結構。我們不但要靜态地研究結構形态;還要動态地研究結構生成;微觀研究結構成分;宏觀研究結構網絡。結構主義領袖皮亞傑認為:“一個結構包括了三個特性:整體性、轉換性和自身調整性。”整體性指若幹成分建構體系的組成規律;轉換性指結構是動态的轉換體系(而非靜态的形式);自身調整性指結構轉換不會越出結構邊界之外,具有守恒性和某種封閉性。亞裡士多德最早指出文學的叙事結構即情節安排,他認為悲劇情節應有頭有尾(完整)并有長度(時間延續過程)。
傳統叙事作品中情節結構占主體地位,最典型的是戲劇沖突的結構:序幕—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尾聲。結構主義建立了“中心化結構”,而解構主義堅決反對中心化,認為中心“不是一個固定的點,而是一種功能,一種使無數符号替換物的活動成為可能的無定點”,他們從“作品”走向“本文”。巴特認為“本文無所謂構造,本文中的一切都一次次得到意指和多次運用,本文沒有一個極盡的整體,也沒有終極結構。”他還認為,“根本不存在文學獨創性這種東西……所有的文學都是互為文本的”。
叙事結構
電影的叙事結構也有多極(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指組織關系和表達方式,可稱為本文結構或總體結構,它與蒙太奇結構含義相當,是影片的總體架構方式,包括“潛結構、策劃、設計、烘托以及作為結果的對形式與内容的總體感覺”(薩·托馬斯語),叙事結構是影片生命的骨骼和軀幹,是其面貌和風格特征的最重要的方面;第二個層面指電影整體系統的組織關系,如類型片結構模式,它在總體結構之上;第三個層面在總體結構之下,即影片内部各元素的組合關系,如情節、畫面、剪輯組合關系。
總之,電影叙事結構參與元素更多,因而更複雜,需有精細的情節設計和精巧的結構布局才能講好故事。新浪潮所創的“無結構”其實是一種更隐蔽、自由而松散的結構。結構并非直觀可見的對象,一般觀衆難以分析,這正是對電影作叙事結構模式分析的意義所在。通過結構模式分析,便于把握電影叙事構成的一般規律和創新途徑,使創作者和觀賞者在結構本文和解讀本文時有章可循、提綱挈領。結構隻是形式,與它同樣重要的密不可分的是内容,因此分析結構模式離不開對内容的理解。
以上并非全部結構模式,也不純粹,模式交叉變異也較常見,它們并無高下之分,隻有更适合于内容的模式而不存在最佳模式。第一種模式形成了強大的叙事傳統,受戲劇和古典小說影響大,其它模式的多元化正是電影擺脫傳統叙事影響而成為獨立藝術門類的努力之一,故可統稱“非戲劇式非線性結構”。
總結
叙事結構就像是支撐一座現代高層建築的主梁結構:你看不到它,但它卻決定了你構思的作品的輪廓和特點。然而小說結構的影響不是在空間上,而是在時間上—往往是經曆很長的時間之後才能讓人感受到。柯勒律治認為在文學史上有三個最著名的情節。亨利·菲爾丁的《湯姆·瓊斯》就是其中之一(另兩個都是戲劇,即《俄狄蒲斯王》和本·瓊森的《煉金術士》)。這部小說的企鵝版長達九百頁,如前面(第三十六節)提到的,它有一百九十八章,分作十八卷。前六卷的背景是在鄉下,接下來的六卷背景是在路上,最後六卷的背景是在倫敦。
在小說的正中間,大部分的主要人物都路過同一個客棧,但相互間沒有碰面,否則故事就無法再寫下去,而隻得早早地收尾。全書充滿了驚奇、神秘和懸念。結尾用的是古典式的手法:真相大白、被颠倒的事實得到匡正。要說明這樣一個複雜情節的作用,僅僅用一些簡短的引文是不夠的。但是美國作家列奧納德·邁克爾斯創作了一些據我所知是最短的小說,他的小說使我們可以在濃縮的作品裡仔細考查這個過程。我有意識地做了點假,因為這裡給出的幾個片斷原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屬于一組短篇小說,它們的總标題是“外出就餐”。其中的一些故事相互聯系,因為它們所描寫的是同一個人物或同一些人物。比如《媽媽》講述的是叙述者和母親間的系列對話故事中的一個。
相互關聯的整個一組故事的意義要大大超過它的組成部分的總和。然而,每一部分都是一個獨立的故事,有各自的标題。即便脫離了上下文,《媽媽》的意思也很清晰:這位猶太母親總是作最壞的打算。這一文本或許介于故事和笑話之間,但《手》一文的歸屬問題非常明确,它完全符合古典作家提出的有關叙事整體性的觀點。正如亞裡士多德所定義的那樣:它有一個開頭,一個中間部分和一個結尾:開頭不要求有任何内容在它前面出現,結尾不要求有任何内容在它後面出現,而中間部分前面要有開頭,後面要有結尾。
《手》一文的開頭由最前面的三個句子組成,描寫的足叙述人懲罰兒子的事。我們不需要知道兒子闖了什麼禍招來了父親的懲罰。第一句話“我掴了兒子幾巴掌”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熟悉的家庭背景。叙述者的情感是重點強調的内容。“我憤怒異常。就像法官一樣。”這個無動詞句是一種事後的思考,是作者為緩解緊張局面、行使他作父親的權力所作的辯解。
故事的中間部分描寫了叙述者逐漸地對他的正當行為失去了信心以及他為自己對兒子的所作所為作辯護的企圖。首先有一種身心失調的症候:“然後我發現自己的手麻木了。”對于這位“毫無感覺”的父親,手既是一種舉隅用法(一種修辭用法,是用部分代全體,或用全體代部分),又是一種隐喻用法。
“我說:‘聽着,我想把這複雜情況解釋給你聽聽。’”從結構上說,整個故事都以這惟一的直接引語為軸線。從形式上講,這種引語對叙述者非常有利。因為直接引語比間接引語更能說明說活人的存在這層意思。但是對一個小孩用“複雜情況”這樣一個成年人的字眼卻洩露了天機。盡管他公開表示了想同兒了交談的急切心情,“我說話嚴肅審慎,當父親的都這樣。”但叙述者私下裡卻在同他自己的良心較量。
結尾部分包含兩重對仗工整的颠倒:首先,事實證明小男孩有敏銳的洞察力,一下子就看透了父親的心思:“等我解釋完,他問我是否想讓他原諒我。”其次,父子間正常的權力關系颠倒了:“我說是的。他說決不。”這些句子的對稱性同情節的對稱是遙相呼應的。叙述者說“聲音像喇叭”,他沮喪地承認了自己的失敗。
亞裡士多德的現代追随者R·S·克雷恩把情節定義為“一個完成了的變化過程”。然而許多現代小說卻要避免“完成了的”這個詞所暗含的那種結束,而着重描寫狀态變化之小。
《合适》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它的叙事結構比《手》更令人難以捉摸—更隐晦、更難領會;開頭、中間和結尾的界限更不明确。它運用了我前面在“浮在表面”和“暗示”兩節裡所讨論過的寫作技巧,幾乎全部由對話組成,隐瞞了人物的想法和動機。我們可以推測這對夫婦止進行某種異常的性行為,但是我們不可能也沒必要知道它到底是什麼。開頭部分,這位婦女抱怨自己感覺不舒服;中間部分叙述者進行了自我辯解,而他的妻子又重申了自己的觀點(“對我來說這簡直糟透了”);結尾部分她拒絕接受這種淺薄的性遊戲。
但是它沒有像《手》一文那樣明确點明叙述者将面臨的嚴峻考驗。我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告訴我們這個故事,因為他隻是轉述了這位妻子對他的嚴厲指責而未加評論。《手》讓人一目了然,而我們要理解《合适》一文卻不得不一遍遍地讀,費盡心思,細細品味。(“她說:‘喜歡我不喜歡的…我電活不到感覺合适的那一天。’”)作品似乎是寫僵局而不是寫發現的,其統一性主要是靠它内部詞彙的前後呼應,尤其是一再重複标題中突出強調的“合适”一詞,而不是靠它的叙事結構。在這方面,它倒像首無韻詩—要不就像是一部長篇小說的一個撩撥人的片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