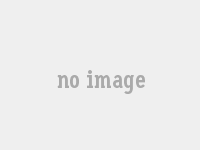内容分析
泰戈爾在《沉船》中的确描寫了許多“好人”,但内容并不象人們想象的那樣,是一個“好人世界”。泰戈爾對“好人”的理解與我們完全不同。他筆下的許多人物都是有缺陷的“好人”,還不是我們心目中那種理想化的“好人世界”。泰戈爾更多地表現了這些“好人”在現實世界中的尴尬與不足,并沒有美化或虛構任何理想化人物。
如安那達先生愛女兒,急于讓她與羅梅西結婚,實際是激化了羅梅西、漢娜麗妮和卡瑪娜三人間的矛盾;如果他多給羅梅西一些時間,矛盾可能會緩解得多;再如卡克拉巴蒂大叔好心誤事,明明想幫助他人,卻給羅梅西與卡瑪娜添了不少麻煩;羅梅西的父親為了報恩,就包辦了兒子的婚事;納裡納克夏的母親由于自己喜歡漢娜麗妮,就鹵莽地為兒子定下親事。這些都表現了好人的“尴尬與不足”。他們想成人之美,但結果卻适得其反。
對照泰戈爾<飛鳥集>中的詩句,我們就會明白作者的這種深意:“太急于做好事的人,反而找不到時間去做好人”。當你硬把幸福給予别人時,這幸福很可能成為他們身上的負擔。就象《飛鳥集》中說的那樣,“鳥的翅膀系上了黃金,這鳥兒便永不能再在天空翺翔了。”
事實證明,這些出于“好心”的“好事”,實際上都很可能是“壞事”。在某種意義上,作品中的許多人物大都是有待完善的對象。如納裡納克夏的母親,是一個虔誠于宗教的女性,心地固然不壞,但性格刻闆,思想頑固,類似于一個被宗教儀式化了的生命。作者在行文之中,流露出對這個形象的某種喜愛,但也有一定程度的批評聲音。
所以,不能斷定泰戈爾美化了現實世界。事實上,光有這些好人的“好心”,兩對青年男女的苦難是無法得到解決的。這兩對青年男女是“好人”,但在作者眼裡,他們是“成長中的好人”,婚姻錯位的遭際并不是人間“苦難”,而恰恰是人生“課程”。也就是說,這些人物最初很可能并不是完美的,恰恰是需要道德完善的生命。泰戈爾強調的是人心靈境界的無限拓展。他的視線并沒有停留在個人的幸福或愛情之上。
對于漢娜麗妮來說,這個被嬌寵慣了的女子需要從個人的痛苦中走出來,進一步拓展自身的世界。如果羅梅西陪伴在身邊,她是不可能獨立成長的。這就是她與羅梅西暫時分離的客觀原因;而她的思想又不可能自行升華,這就是她與納裡納克夏有一段“臨時”婚約的根本原因。不離開羅梅西,她就不可能真正獨立;而不走近納裡納克夏,她也不可能受到思想上的啟迪,并獨自戰勝生活中的坎坷。
對于羅梅西來說,他應該從追求幸福的個人角色中掙脫出來,進一步将自己融入到社會中去,去關愛更多不幸的人們,就象納裡納克夏那樣。因此,命運将需要照看的卡瑪娜送到了他的身邊,并讓他在關愛他人的責任追求個人幸福之間做出選擇。他要通過舍棄自身幸福去關愛他人,并以此提升自己的心靈境界。這就是他與漢娜麗妮的愛情為什麼會遭遇“誤會”的内在原因。
作者簡介
羅賓德羅那特·泰戈爾是印度著名詩人、作家和哲學家;而且在音樂和繪畫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他于一八六一年生于孟加拉一婆羅門地主家庭,一八七七年到英國學習法律,但不久棄學歸國,經營其父遺産,并開始從事文學和哲學創作活動。他一生共寫了五十多部詩集,二十多部劇本,十二部中篇和長篇小說,一百餘篇短篇小說及其它着作(包括哲學着作和各種論文集)達四十卷。哲學着作以《生之體現》最為重要,該書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傳統的印度哲學思想。詩集最著名的有《吉檀迦利》、《園丁集》、《新月集》、《飛鳥集》等。
泰戈爾曾于一九一三年,主要以其詩集《吉檀迦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戲劇較重要的有《郵局》、《紅色夾竹桃》等。他的作品主要用孟加拉文寫成,其中大部分由他本人譯成英文。
泰戈爾在印度享有極高的聲譽。泰戈爾雖自幼接受西方資産階級教育,但在宗教、哲學、社會思想等方面仍具有濃厚的東方色彩。他十分崇拜古印度詩人迦梨陀娑,對古印度梵文文獻相當熟悉。對于西方文明,他一方面贊賞其完成實際工作的能力,同時又頗惡其精神空虛。他顯然完全接受性善說觀點,視幼小男女天真無邪的心靈至為可愛和可貴,切望人人都保有赤子之心。他主張恬靜、淡泊的生活,反對激情;主張人與人和睦相處、彼此相愛相助,樹立人類為一整體的觀念,反對互相歧視、欺淩和使用暴力。
在這樣一些思想支配下,他一方面對印度特有的種姓制度等不合理現象深惡痛絕,另一方面又必然反對暴力革命,甚至對印度本身的民族解放鬥争也持否定态度,提出了于人民有實惠的社會改革更重于空洞的政治自由一類口号。泰戈爾本人曾長期緻力于和平運動。一九○一年他在聖谛尼克坦創辦了“和平之家”(一九二一年易名為“國際大學”),招收世界各國學生,學習有關社會改革、國際團結及農村建設等方面課程,所獲諾貝爾文學獎金全部用作學校經費,希望借此實現其世界和平理想。
泰戈爾于一九四一年去世。
阿爾丁夫
中國當代著名詩人阿爾丁夫.翼人的長詩《沉船》中英文對照版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由天津師範大學教授、著名翻譯家張智中翻譯,著名詩歌評論家霍俊明作序,并收有著名詩歌評論家李犁、吳投文的專論。《沉船》被譽為“人類前行的精神簡史”、“民族精神的詩歌化石”、“不斷淬煉的精神升階書”等。
《沉船》從我國少數民族撒拉族的曆史出發,抒寫了一個民族800年的遷徙史、苦難史和民族性格的生成史。詩人對撒拉族在曆史長河中的掙紮、遷徙、繁衍的曆史境遇與苦難命運的抒寫,是一個民族蒼涼悲歌的絕響,構成了一個民族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的的生存史和心靈史的曆史畫卷,從這個意義上說,《沉船》是當下漢語詩歌創作中一部具有準史詩品格的長詩,在中國的長詩寫作版圖中具有啟示錄的價值和意義。
從語言上看,《沉船》的語言蒼涼、沉郁,極具質感與個性;從精神向度上看,詩集對曆史的反思與诘問令人發聩,彰顯了一位詩人的詩學主張、精神立場與人文情懷;從藝術手法上看,詩人從一個民族的生存與命運的觸角對曆史進行縱橫切割,為當代漢語詩歌深入曆史與存在,從容地處理曆史經驗提供了極有價值的思考與借鑒。
《沉船》全詩共有56節。《沉船》運用浪漫主義、象征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等多重手段,結構成集理想、美學與批判為一體的詩意外化物,從民族傳統的審美和思想兩個角度考察,這部《沉船》在進行着“史詩是人文史與精神史的合璧”的探索。
詩人李犁評價道:這是一條從遠古駛來的大船。船體已經破舊,有些零件也發生了故障。它拉載的是一個民族,穿過了黑夜和蒙昧,終于獲得了自由和文明。這個民族本身就是一條大船,有着滄桑和苦難,光榮和夢想,但到了今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和迷茫。
這是一部悲天憫人的大詩。作者用自己充沛的元氣和大氣吟唱它所經曆的黑暗與光明、死亡與誕生、野蠻與文明、屈辱與尊嚴、流血與和平,還有未來與期待。作為撒拉爾的後裔,翼人主動用他的英雄氣質為這個民族奏一曲磅薄的史詩。從這個意義來說,它也是更多民族、國家,甚至人類在漫長的歲月中緩緩前行的簡史。所以它的意義越過詩歌本身,進入到對人類的現狀和未來的思考和诘問。
詩人、作家及評論家沙克認為,沉重、悲壯、熱血、迷狂,是《沉船》追索永在之物的集中表達。
當宏大抱負的含量大于一件文本,詩歌題旨便顯得沉重,成為深厚的基礎;當文化尋根的途徑過于艱險,詩歌意象便顯得悲壯,成為精神的圖騰;當求達彼岸的心願特别迫切,詩歌情緒便顯得熱血,成為獻祭的奠儀;當信仰程度強于藝術表現,詩歌書寫便顯得迷狂。《沉船》運用浪漫主義、象征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等多重手段,結構成集理想、美學與批判為一體的詩意外化物,從民族傳統的審美和思想兩個角度考察,這部《沉船》在進行着“史詩是人文史與精神史的合璧”的探索。
《沉船》的出版,為當代詩壇提供了“民族書寫與個性書寫相結合”的一份經驗,同時也呈現了史詩性實驗的一份樣本。
長詩
無論在現代詩的主題,還是在現代詩形的創造上,阿爾丁夫·翼人都是卓越獨異的探索者。他鐘情于長詩,他的長詩猶如屹立的長城、流動的黃河,湧動着一個中國民族詩人身上的史詩血脈。他的詩歌浩瀚遼遠,波谲雲詭,通過整體的象征造成一種詩歌意象與意境上的神秘和尊貴,這使他的詩篇猶如面對人間的“神示”,散布着宗教般的光芒,照亮了世界的此岸與彼岸。在翼人那裡,時間和空間、存在和哲理、生命和死亡、瞬間與永恒、自我與他者……所有這一切交織在他的詩歌裡,構成了一幅原始與現代、頹廢與新生、激情與憂郁、敞開與内斂、明亮與晦暗……不同元素對抗着的充滿張力的畫面。在他的詩歌裡,至今充溢着罕見的詩歌熱情。是的,他是一位足以令我們感到驕傲的詩人,但他更屬于整個人類。
阿爾丁夫翼人
阿爾丁夫·翼人,當代著名詩人。撒拉族,又名容暢、馬毅。1962年出生,祖籍青海循化。曾先後畢業于青海教育學院英語專業、西北大學漢語言文學系,現任世界伊斯蘭詩歌研究院中國分院院長、國際漢語詩歌協會秘書長、《大昆侖》雜志主編、青海大昆侖書畫院院長、青海民族文化促進會會長等。
代表性作品有史詩性長篇詩歌《飄浮在淵面上的鷹嘯》、《沉船》,《緻伊朗》、《河流:我的青銅塑像》以及《蒼茫瞬間:播種時間的美》、《荒魂:在時間的河流中穿梭》、《母語:孤獨的悠長和她清晰的身影》等。
作品入選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屆《青海湖國際詩歌節詩人詩選》、《2010世界詩歌之窗》(波斯英語雙語版)、《2012世界詩人詩選》、《21世紀中國詩歌排行榜》、《詩刊社2011年度詩選》、《中國當代詩歌導讀·2010卷》、《中國現當代傑出詩人經典賞析》、《2011年中國詩歌排行榜》、《中國當代十家傑出民族詩人詩選》、《2012中國詩選》《印度尼西亞與一位中國詩人》、《母語之外的母語》、《中韓作家作品選》、《中國新詩300首》(1917——2012)、《世界詩人詩選》等。
出版詩集《被神祇放逐的誓文》、《沉船》(英漢對照版),主編有《中國西部詩選》、《撒拉爾的傳人》(第一、第二輯)等。詩作已被譯成英語、西班牙語、俄語、孟加拉國語、德語、韓語、波斯語、羅馬尼亞語、馬其頓語、印度語等多種文字發表和出版。
作品曾先後榮獲“中國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中國當代十大傑出民族詩人詩歌獎”、“中國當代詩歌創作獎”“國際最佳詩人獎”及“第十一屆黎巴嫩納吉·阿曼國際文學獎”等。
2010年他應伊朗國家文化部邀請參加“德黑蘭首屆國際詩歌節”,受到艾哈邁迪-内賈德總統的親切接見;曆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屆)參加“青海湖國際詩歌節”;2011年随中國作家協會作家代表團出訪美國,2012年9月赴以色列參加“第32屆世界詩人大會”。
阿爾丁夫翼人
——論阿爾丁夫·翼人的長詩《沉船》(代序)
霍俊明
長詩無疑屬于更有難度的詩歌寫作類型,而中國又是自古至今都缺乏長詩(史詩)寫作的傳統。自海子之後中國詩人的史詩情結多少顯得荒涼、青黃不接,而寫作長詩甚至“史詩”一直是從“今天”詩派、第三代詩歌以及90年代詩歌以來當代漢語詩歌噬心的主題,甚至在海子之後隻有極少數的詩人敢于嘗試長詩的寫作,其成就也是寥寥。因為寫作長詩對于任何一個詩人而言都是一種近乎殘酷的挑戰,長詩對一個詩人的語言、智性、想像力、感受力、選擇力、判斷力甚至包括耐力都是一種最徹底和全面的考驗。在筆者看來“長詩”顯然是一個中性的詞,而對中國當代詩壇談論“史詩”一詞我覺得尚嫌草率,甚至包括海子在内的長詩寫作,“史詩”無疑是對一個民族、國家、曆史、文化的多元化的書寫和命名,而這是對詩人甚至時代的極其嚴格甚至殘酷的篩選的過程。
在一個工業化的時代會産生重要的長詩,但是“史詩”的完成還需要時日甚至契機。在筆者看來“大詩”正是介于“長詩”和“史詩”之間的一個過渡形态。說到當代的“長詩”不能不提到幾位重要的詩人,洛夫、昌耀、海子、楊煉、江河、歐陽江河、廖亦武、梁平、于堅、阿爾丁夫·翼人、大解、李岱松(李青松)以及江非等更為年輕的詩人。我從不敢輕易将當代詩人包括海子的長詩看作是史詩,我們的時代也不可能産生史詩,我更願意使用中性的詞“大詩”。我更願意将當下的後社會主義時代看作是一個“冷時代”,因為更多的詩人沉溺于個人化的空間而自作主張,而更具有人性和生命深度甚至具有宗教感、現實感的信仰式的詩歌寫作成了缺席的顯豁事實。
在中國1990年代以來的“長詩”寫作版圖上,阿爾丁夫·翼人的長詩寫作具有啟示錄的價值和意義。但似乎有很多專業研究者對他以及他多年來的長詩寫作缺乏必備的了解。
在後社會主義時代的今天,阿爾丁夫·翼人大量的長詩寫作,如《沉船》、《神秘的光環》、《錯開的花裝飾你無眠的星辰》以及《漂浮在淵面上的鷹嘯》、《放浪之歌》、《古棧道上的魂》、《西部:我的綠色莊園》、《撒拉爾:情系黑色的河流》、《蜃景:題在曆史的懸崖上》、《遙望:盛秋的麥穗》等都秉承了一以貫之的對宗教、語言、傳統、民族、人性、時間、生命以及時代的神秘而偉大元素的純粹的緻敬和對話,這種緻敬和對話方式在當下暧昧而又強橫的後工業時代無疑是重要的也是令人敬畏的,“子不予怪力亂神/——撒拉爾/在這前定的道上/壯行獨美八百年/而這道啊!注定/以尕勒莽阿合莽的名義/鑄造黃金般的誓言/靈魂像風奔跑在美的光影裡”(《靈魂像風奔跑在美的光影裡》)。
阿爾丁夫·翼人的這種帶有明顯的民族和詩歌的雙重“記憶”的不乏玄學思考的詩歌寫作方式和征候不能不讓我們聯系到海子當年的長詩寫作。但是海子的長詩在最大的程度上祛除了個人的現世關懷和俗世經驗,這就使海子的長詩拒絕了和其他個體的對話和交流并也最終導緻了在無限向上的高蹈中的眩暈和分裂。而可貴的是阿爾丁夫·翼人多年以來的長詩寫作是同時在宗教、哲理、玄學、文化和生命、當下、時代和生存的兩條血脈上同時完成的,這就避免了其中任何一個維度的單一和耽溺,從而更具有打開和容留的開放性質地和更為寬廣深邃的詩學空間。撒拉爾、清真寺、駱駝泉、先民陵墓、古蘭經以及青藏高原和黃土高原的接合部、黃河之畔的循化都成為詩人永遠無眠的星辰和恒久的詩歌記憶,“我剛剛從兩莽的墓地歸來/兩膝的黃土翻滾着/曆史的煙雲在我眼前紛飛/我鬥膽以卑微的思想/想像上千年兩河流域的文明/和兩莽直逼中西文化的巨人的光芒”(《錯開的花裝飾你無眠的星辰》)。
從理想主義、集體主義的紅色政治年代過渡到商業化、娛樂化、物欲化、傳媒化的後工業的強權時代,劇烈的時代震蕩和社會轉變,夾縫中生存的尴尬和靈魂信仰的缺失都如此強烈地淤積在翼人以及同代人的内心深處,甚至一些更為強烈的傾訴和抗議的願望已不可能在短詩中加以完成和淋漓盡緻地呈現,隻能是在長詩寫作中才能逐漸完成一代人的傾訴、對話、命名和曆史的焦慮,磅礴大氣和溫柔敦厚并存的詩歌方式成就了翼人長詩的個性。概而言之我們看到包括翼人在内的一些詩人寫作長詩的努力印證了中國當代詩人寫作優秀長詩的可能性,盡管其面對的難度可想而知。
當然這種可能性隻能是由極少數的幾個人來完成的,曆史總是殘酷的。在巨大的減法規則中,掩埋和遺忘成了曆史對待我們的态度,而語言和詩歌永遠比一個國家更古老,更具有生命力,一些詩人用語言創造的自我和世界最終會在曆史中停留、銘記,曆史在尋找這個幸運者,這個幸運者肯定也是一個在個人和時代的軌道上發現疼痛和寒冷的旅人。作為60年代初出生的詩人,阿爾丁夫·翼人的個性使其詩歌寫作中具有強烈的文化尋根(同時具備了農耕文明和遊牧文化)和民族叙事的抒寫沖動。
作為一個撒拉爾族人,阿爾丁夫·翼人很容易被看作少數民族詩人,因為身處青海又更易于被貼上“西部詩人”、“邊地詩人”的标簽。當然無論是将阿爾丁夫·翼人看作少數民族詩人還是西部詩人,這都無可厚非,甚至這種民族根性和西部的文化地理學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阿爾丁夫·翼人的詩歌寫作個性,尤其是他的長詩寫作譜系。
但是我更願意在更為寬廣的意義上看待翼人的身份和長詩的個性,因為他的長詩寫作在當下的時代具有明顯的詩學啟示錄的價值和意義。當然這并非意味着翼人的長詩寫作就是毫無缺點和無懈可擊,而是說他多年來的長詩無論是對于中國當代長詩的寫作傳統還是一般意義上的詩歌寫作而言确實具有着需要我們重新認知的埋藏着豐富礦石的地帶。
翼人的的長詩寫作呈現的是既帶有神秘的玄學又帶有強烈的與現實的血肉關系的質地,無論是與詩人的生存直接相關的往事記憶、生活細節還是想像和經驗中的更為駁雜的曆史性、民族性和宗教性的場景、事件,這一切都在融合與勘問中呈現出當下詩人少有的整體感知、曆史意識、人文情懷和宗教信仰。
翼人的長詩寫作在張揚出個體對自我、世界、生存、詩歌、曆史、民族、宗教的經驗和想像性認知的同時,也以介入和知冷知熱的方式呈現出工業和城市化語境之下傳統的飄忽與現實的艱難,尤其是急速前進的時代之下駁雜甚至荒蕪的人性與靈魂。翼人多年來的長詩踐行更像是一個個人化、曆史化、生命化和寓言化的精神文本和一個詩人的靈魂升階之書。
而1990年代以來,一些詩人普遍放棄了集體或個人的烏托邦“儀式”而加入到了對日場經驗和身邊事物的漩渦之中。當我們普遍注意到90年代詩歌的叙事性和日常經驗的呈現時,為詩人和研究者所津津樂道的詩歌的“個人化”(私人化)風格卻恰恰在這一點上獲得了共生性和集體性。在一定程度上随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社會語境和相應的詩歌寫作語境的巨大轉換,詩歌寫作對以往時間神話、烏托邦幻想以及“僞抒情”、“僞鄉土寫作”的反撥意義是相當明顯的,但是這種反撥的後果是産生了新一輪的話語權力,即對“日常經驗”的崇拜。
确實“日常經驗”在使詩歌寫作擁有強大的“胃”成為容留的詩歌的同時,也成為一種巨大的漩渦,一種泛濫的無深度的影像仿寫開始彌漫。基于此,翼人不能不在詩歌寫作中形成這樣的體認,即對于大多數詩人而言,應該迫使自己的寫作速度慢下來并具備開闊的視野和對現實與曆史的強大的穿透力和反觀能力,從而最終達到與生存與時代相契合的精準而真實的聯系和見證意義,“或許我們本不該再次久留/本不該扶你送上祭壇/周圍的一切都在蒙昧的花園裡/投去鄙視的目光扼殺或挫敗/無與倫比的夢幻在世界的中心旋轉”(《神秘的光環》)。
對于在詩路跋涉、探詢、挖掘的翼人而言,在黑夜的明滅閃爍的火光中揭開詩歌漂流瓶,在物欲、金錢、權利和瘋狂幻象圍攏、擠迫的黑暗中沉潛下來,傾聽來自語言、民族、宗教以及遙遠而本真的靈魂獨語或對話的神秘召喚是一種不能放棄的責任與擔當情懷。
這一切無疑是良知的體現,正如布羅茨基所說“詩歌是對人類記憶的表達”,而從“詩”的造字含義上就含有記憶和“懷抱”以及宗教的精神維度。正是在此意義上翼人的長詩寫作真正回到了詩歌的源頭。他制造的詩歌漂流瓶盛滿了集體的記憶積澱,而那明滅閃爍的火光中本真的甯靜與自足閃現就是必須的,是傾盡一生之力追問和挖掘的高貴姿态。巴什拉爾說“哪裡有燭火,哪裡就有回憶”,是的,哪裡有傾聽,哪裡就有回憶。基于此,翼人在“深入當代”與“深入靈魂”的噬心主題的獨标真知的籲求中彰顯出執着的詩學禀賦和富有良知的個性立場,以詩歌語言、想像力和獨創的手藝承擔了曆史和人性的記憶。
翼人的長詩中持續不斷的是詩人對天空、河流、土地、山脈、彼岸和精神烏托邦世界(當然也是個人化的)的長久浩歎與追問,這種源自于詩人身份和民族記憶的對詩意的精神故鄉的追尋幾已成為他詩歌寫作的一種顯豁的思想特征甚至征候。對于優秀的詩人而言,在後工業時代語境之下堅持一種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的探詢和诘問是最為值得尊重的一個維度,我是在整體性上來談論翼人與理想主義、農耕文明、宗教情懷之間的尴尬和挽留關系的。
翼人自1980年代以來的詩歌寫作尤其是長詩寫作,确實蘊含了一種獨具個性而又相當重要的個人化的曆史想像力和深入現實的精神向度。這種個人的曆史想像力較之1980年代以來的帶有青春期寫作症候的美學想像力而言更具有一種深度和包容力。曆史想像力是指詩人從個體主體性出發,以獨立的精神姿态和話語方式去處理生存、曆史和個體生命中顯豁和噬心的問題。換言之曆史想像力畛域中既有個人性又兼具時代和生存的曆史性。
曆史想像力不僅是一個詩歌功能的概念同時也是有關詩歌本體的概念。翼人詩歌寫作尤其是長詩寫作,有力地在曆史想像力的啟示下呈現了一個民族的精神肖像和一代人的詩歌史、生活史。這些詩作也可以說是曆史想像力在一代詩人身上的具有代表性的展現與深入,清醒與困惑的反複糾纏,自我與外物的對稱或對抗。
翼人的詩句有如長長的沉重的鐵鍊頑健地拒絕鏽蝕的機會,那抖動的铮铮之聲在午夜暧昧而強大的背景中呈現為十字架般的亘古的凜冽和蒼涼,“哦,沉默的土地啊/那是從遙遠的馬背上啟程的兒子/亘古未曾破譯這現實時間的概念/或有更多的來者注視:存在的背後/所蘊含的哲理被輕柔的面紗遮去/或是老遠望去河岸的大片風景/在絢麗的陽光照耀下步步陷入深淵”(《沉船》)。
這些容留的力量、張力的沖突及其攜帶巨大心理能量和信仰膂力的詩句,在當下詩人的詩歌寫作中是相當罕見的。這也隻能說明在曆史與當下共同構築的生存迷宮和怪圈中,特殊的生存方式、想像方式和寫作方式造就了一個張揚個性、凸現繁複鏡像和無限文化與傳統“鄉愁”的詩人翼人,“在你面前我曾是一名無望的患者/使我重新确認物體的表面所蘊含的重量/遠遠超過草木細微的影子/或許這僅僅是傳說或許我們早跟自己的影子相逢/且在光明的路上拖着尾巴/穿過大街小巷或那無盡的回憶/并把所有的夢想化為石頭的訓語/镌刻靈魂緘默的花樹”(《神秘的光環》)。
在一個信仰中斷和放逐理想的年代,在一個鋼鐵履帶碾壓良知和真理的粉末狀的年代,一個跋涉在精神之路上的歌手,一個不斷叩問的騎手在工業的山河中與風車大戰。因此,翼人的詩歌更為有力地呈現了時間的虛無和力量,換言之在具體的細節擦亮和情感的呈示中翼人的長詩更多顯現的是詩人對時間和生存本身的憂慮和尴尬,在茫茫的時間暗夜這短暫的生命燈盞注定會熄滅,曾經鮮活的生命在幹枯的記憶中最終模糊,“唯有你們/早晚在崇高詩篇的頌聲中/平安度日再度忙碌/也不忘時刻的準點/嚴守時間的秘密/把最神聖的交換托付”(《錯開的花裝飾你無眠的星辰》)。有人說誰校對時間誰就會老去,但是翼人卻在蒼茫的時間河流上最終發現了時間的奧義和神秘的詩篇。
所以多年來翼人的長詩寫作無論是在精神型構、情緒基調、母題意識、語言方式、抒寫特征還是想像空間上,它的基調始終是對生存、生命、文化、曆史、宗教、民族、信仰甚至詩歌自身的無以言說的敬畏和探詢的态度,很多詩句都通向了遙遠的詩歌寫作的源頭。
這無疑使全詩在共有的閱讀參照中更能打動讀者,因為這種基本的情緒,關于詩歌的、語言的和經驗的都是人類所共有的。這種本源性質的生存整體共有的精神象征的詞句不時出現在長詩之中,這在某種程度上帶有向傳統、語言、詩歌的緻敬和持守意味,“相信或懷疑注有标記的旗杆上走動的人群/在我的耳旁号叫、嘶鳴/但我依然守候着他們/當他們遠離親人時/吹送柔柔的清風”(《沉船》)。
精神尋根的詩性觀照
—論阿爾丁夫·翼人的長詩《沉船》
吳投文
從早期白話新詩的起步開始,長詩似乎就不斷地遭遇困境,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概而言之,大概包含這樣幾方面:一是中國向來缺乏長詩傳統,這可以看做是一種源頭性的缺失,對新詩的影響甚大,但新詩研究在此方面沒有做系統而深入的清理;二是長詩缺乏清晰的邊界,到底多長才算長詩,一直沒有定論,實際上也很難達成統一的意見,這是在創作和研究的實際操作中面臨的一個難題,長期以來衆說紛纭,這對長詩創作無疑會帶來某些不利的後果;三是長詩在“長度”之外,還在内涵與結構上有一些特殊要求,這又很難達成共識。
此外,還有一些更深層的原因有待探讨,但在新詩創作和研究中卻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長詩的曆史價值與藝術定位也往往比較模糊,不能在文學史格局中獲得獨立的身份認定,也就不能充分彰顯自身的藝術特性,這樣,長詩的美學特質也就不能凸顯出來。
但值得注意的是,長詩創作又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在中國新詩史上,也不乏氣象闊大的長詩傑作。著名詩評家葉橹先生極有見地地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始終不能出現能夠抒寫傑出偉大的長篇詩歌的大手筆,必定是這個國家和民族的一種缺憾和悲哀。”
葉橹:《呼喚長詩傑作》,為洛夫主編《百年華語詩壇十二家》一書所寫的序言,台海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1頁。)可以說,長詩具有精神界碑的性質,能夠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精神高度。長詩寫作也是極富挑戰性的創造工程,大概也是檢驗詩人才華與心智的一個重要指标,因此,有創作雄心的詩人往往會向長詩發起挑戰,殚精竭慮地投入到長詩創作中來。實際上也是如此,在長詩創作上取得成功的詩人,更容易引起讀者的關注和受到研究者的重視,這大概也是很多詩人傾注全部心力投入長詩創作的一種隐秘動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來讨論撒拉族著名詩人阿爾丁夫·翼人的長詩《沉船——獻給承負我們的歲月》,也許能找到進入文本内部的某種依據,同時呈現出這部長詩的獨特價值。從阿爾丁夫·翼人的寫作曆程來看,他成名頗早,是當代中國詩壇的一位實力派詩人,尤其在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界具有非常廣泛的影響,先後獲得青海省人民政府第四屆文學作品獎、中國第四屆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中國當代十大傑出民族詩人詩歌獎”等重要獎項。
從他的主要創作來看,長詩代表其創作成就的一個重要方面,近三十年來他一直緻力于長詩創作,史詩性長詩《飄浮在淵面上的鷹嘯》、《沉船——獻給承負我們的歲月》等就是當代長詩創作有代表性的成果。他的創作路子顯示出自己獨立的藝術追求,沒有被詩壇的流行色所遮掩,要做到這一點實際上并不容易,從中可以發現阿爾丁夫·翼人詩歌創作尋求創新的藝術自覺和獨特的藝術情思。
當我們把目光聚集到長詩《沉船——獻給承負我們的歲月》上來,就會感到有一種獨特的氣場籠罩着我們。這是一部在詭異的氛圍中流露出深沉的悲劇意識和清醒的曆史意識和人文情懷的作品,是一部具有廣闊的民族詩史視野的抒情長卷。從長詩的篇幅來看,可謂結構浩大,全詩共五十六節,每節長則二十餘行,短則數行,但大多數介于十行至二十行之間,這不僅使每一節顯得相對勻稱,也使每一節自成精短的篇什,在環環相扣的推進中顯示出渾然一體的藝術效果。
從長詩的整體處理上可以看出作者用心甚深,在長詩中有一個整體性的象征框架,沉船既是一個巨大的隐喻,又是這個整體性象征框架的核心,在長詩中被處理為一種内置性的基本元素,無處不在,但又很少直接道出,這使長詩的主題表現出某種晦暗性,也許不那麼好容易把握,但又同時表現出某種開放性,讓人在詩意的迷宮裡對現實和人生有一種透徹的認識。在我看來,沉船之沉在這部長詩中表現為一種曆史思維和神話思維的渾融化一,詩人的思考帶着嚴峻的曆史反思意識,在詩人蒼勁的筆觸中,民族的曆史和現實都被置于一種犀利而充滿痛楚的審視之中。
就此而言,這部長詩具有精神尋根的意義,詩中有一種回溯性的聲音,這種聲音既是作者個人的,然而個人的聲音似乎又被淹沒在曆史的回聲中,因此,在這部長詩的聲音後面實際上有一個巨大的磁場和空間,值得我們注意。
從長詩的主題内涵來看,似乎是具有多重指向性的,盡管這裡很難對此進行比較清晰的剖析,但也可以從詩中所顯露出來的蛛絲馬迹中發現詩人隐秘的意向。大緻而言,長詩關乎對于曆史的基本理解,卻又具有現實的維度;關乎靈魂的受難,盡管顯得沉痛,卻又并不顯得完全虛無;也關乎對個人命運的理解,其中似乎糾結着一些複雜的情緒,詩人對個體在曆史中的迷失似乎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但另一方面又顯得疑慮和困惑,詩人對個人與曆史的對抗顯然有所期望,但又似乎陷入很深的失落之中。
因此,長詩的主題内涵并不指向一個透明的實體,這表明詩人的曆史感可能是發散性的,也表明詩人對曆史的某種疑慮和對現實的警惕。當然,也有一種在曆史面前的無力感,畢竟曆史是無形之物,也布滿無物之陣,那種吞噬性的力量很容易使人産生恐慌而陷入更深的困惑。長詩在曆史、現實、想象、存在、神話元素所形成的張力結構中,隐含着一個精神尋根的深層意義結構。正如詩人在長詩的“題記”中這樣寫道:
我認識一條河
這便是黃河
這便是撒拉爾
對河流永恒的記憶
和遙遠的絕響
精神尋根表面上看起來是退卻性的,是向虛無中的逃遁,但同時也意味着尋找與皈依,是一種面向自我反思的精神形式,其中也包含着一種健全的曆史理性和現實批判精神。另一方面,這種精神尋根也意味着皈依與拯救,尋根的過程也是一種曆史建構和精神建構的過程,表現為對精神家園的向往,對純粹詩性存在的追尋,這使長詩顯露出一種深沉的現實憂思,而詩中間或出現的荒誕元素,則似乎透露出詩人内心的焦慮,同時也使詩人的憂郁得到放大和強化,也使長詩的主題意向顯露出由精神尋根所帶來的複雜意緒。這在長詩的推進中似乎随處可見:
出門是山
緊閉是河山河喲
世界的本源對于存在者而言
船隊橫對頭頂的浮雲
蒼老地流過——任河的主人驚歎不己
誰的雙腳企圖同時跨進同一條河流?
縱有風暴襲來卻依然保持一絲微笑
瞧苦水包容的思想在你的腹中築巢
阿爾丁夫·翼人筆下的這一闊大場景似乎具有某種提示作用,暗示精神尋根的艱巨過程,也包含着一種豁達的理性精神。實際上,精神尋根在某種意義上也意味着逃亡,而逃亡并不等同于逃避曆史責任和現實擔當,而是尋找救贖和希望,是在反抗的層面上落實一種健全的生命意志。同樣的場景多次出現,隐喻逃亡與精神尋根的某種對應性關聯:
哦,河流生命的絕唱
萬象衆生的意念
世界的象征宛如血色宛如黃昏
宛如廢墟中長出的一枝荷花
以最動人的笑臉四面捭阖
呈現出無數血腥的花朵
逃亡可以說是一個世界性的文學主題,但在不同作家的筆下被處理為不同的文學想象。魯迅的《野草》是作家從茫然到清醒的逃亡,又因過于清醒反而迷失于虛無中,把一種大的哀痛留給讀者而顯示出思想的深刻與銳利,也顯露出作家面對現實難以掩抑的沉痛與矛盾心态;沈從文的《邊城》是作家放逐自我的精神逃亡,出走故鄉湘西固然是一種逃亡,處身都市而又在精神上退回湘西,潛心建構文學的“湘西世界”,同樣是一種逃亡,邊城不過是沈從文心造的幻影,他把現實中感受到的悲哀與沉痛用微笑掩抑起來,把一種似乎愉快的心情塗抹在一片桃花源式的風景中,而他自己則隐遁在一個審美的烏托邦中;
錢鐘書的《圍城》所揭示的現代人的生存悲劇與精神困境,同樣是一個逃亡的主題,不管是城堡中的人,還是城堡外的人,其實都處于精神上的漂泊狀态,而且由于人性固有的弱點,每一個人的内心就是一個封閉的城堡,不僅他人很難進入,其實自己也難以進入。
因此,從本質上說,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孤立的城堡,不僅與他人難以取得溝通,也往往遊離于自己的内心,這樣,人就成為自己的地獄,無法找到真正的精神歸宿,隻能永遠流浪在逃亡的路上,或者在進退之間遊移。在這些作家的參照下,長詩《沉船——獻給承負我們的歲月》中的精神尋根及其伴生的逃亡意識則具有鮮明的當代性。也就是說,長詩《沉船》具有直視當下的問題意識,它并不是一個純然從作者的想象中冒出來的抒情篇章,詩中似乎有一種被壓抑的悲郁,既回蕩着靈魂的被放逐感,又有與現實對接的憂患意識。
詩人阿爾丁夫·翼人從自己的生命體驗出發,既為曆史悲歌,也為現實抒唱,既為自己的民族留下曆史的記憶,也為自我的生命打下來自現實的烙印,因此,長詩的主題意向實際上是展開性的,顯示出複雜的意蘊,對于讀者來說,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應該說,作為一部長詩,《沉船——獻給承負我們的歲月》包含着很多成功的元素,是當代少數民族文學中長詩創作的一個重要收獲。與漢民族文學相比,西北邊地的少數民族文學似乎在長詩創作上有着天然獨特的優勢,顯示出邊地少數民族特殊的藝術禀賦。對阿爾丁夫·翼人來說,他也得益于西北少數民族文學的滋養,尤其是得益于他生于斯長于斯的撒拉族的藝術傳統,這在《沉船》中似乎不難找到通向撒拉族藝術傳統的特殊暗道。這應該是阿爾丁夫·翼人與撒拉族藝術傳統的一次對話,也可以理解為是他對自己民族的一次深情禮贊與緻敬。
同時,從《沉船》中也可以發現詩人得益于域外文學的啟示,長詩中似乎遊蕩着西西弗斯神話的餘音,長詩中的悲涼感顯然與此有關,西西弗斯的巨石是苦難的源泉,既是懲罰,實際上也是重生,在長詩中則轉化為一種清醒的自我發問,難道這塊巨石就是周而複始的徒勞無望的命運的象征?
此外,長詩所展示出來的個人視野也很容易使人産生這樣的聯想:《沉船》的創作也得益于但丁的《神曲》、米爾頓的《失樂園》、艾略特的《荒原》等作品的啟示,阿爾丁夫·翼人大概對這些作品做過用心的研讀,《沉船》中的氣息顯示出詩人接受域外文學啟示的開放性視野。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沉船》的篇幅較大,可以看出詩人刻意經營的苦心,但卻沒有雕琢的痕迹,長詩的主線似乎與詩人情緒的推動息息相關,顯示出結構上的别緻。全詩可謂一氣貫通,如九曲回廊,有一種沉思的靜美,在九百餘行的抒情詠歎中,将個人的心路曆程與民族的精神尋根提煉為一個充分個性化和概括性的詩性形象,作者的藝術抱負值得稱許。
同時,長詩以情緒的流動和升華作為主線的結構方式,盡管有一個精神尋根的象征性構架作為支撐,但由于沒有基本的情節框架作為顯性的叙事标志,讀者也可能一時難以理清長詩的思想脈絡和主題意向。
好在長詩有一種内在的音樂效果,這種結構方式也有利于增強詩歌的藝術張力。就這部長詩的語言來說,作者顯然是有考慮的,既沒有着迷于滿紙晦澀,也沒有停留于直白的傾訴,而是介乎傳統與現代之間,有堅硬的質地和飽滿的張力,長詩的整體節奏與作者的内心情緒協調一緻,即使讀起來也有一種一氣貫通的效果。
詩人一方面似乎懷着憂郁,這使長詩的背景有一種冷抑的底色,另一方面又由于詩人性格上的豪放,詩中又有着内斂的激情,因而長詩的整個基調顯得沉郁悲慨、蒼涼渾厚,有一種打動人心的力量。從整體上看,長詩顯示出詩人對精神尋根的獨特理解,這使《沉船》成為一部具有豐富象征意蘊的作品,這也是其獨特的價值所在。
《沉船》人類前行的精神簡史
李犁
[沉船
這是一條從遠古駛來的大船。船體已經破舊,有些零件也發生了故障。它拉載的是一個民族,穿過了黑夜和蒙昧,終于獲得了自由和文明。這個民族本身就是一條大船,有着滄桑和苦難,光榮和夢想,但到了今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和迷茫。怎麼讓它走出陰霾,不因為自己的腎虧和哮喘而沉沒,這是船長阿爾丁夫·翼人寫作此詩的目的和意義。
作為詩歌顯然這是一部悲天憫人的大詩。作者用自己充沛的元氣和大氣吟唱它所經曆的黑暗與光明、死亡與誕生、野蠻與文明、屈辱與尊嚴、流血與和平,還有未來與期待。作為撒拉爾族的後裔,翼人主動用他的英雄氣質為這個民族奏一曲磅礴的史詩。
從這個意義來說,它也是更多民族、國家,甚至人類在漫長的歲月中緩緩前行的簡史。所以它的意義越過詩歌本身,進入到對人類的現狀和未來的思考和诘問。為了讓這首深奧的詩歌通曉化,本文試圖從這首詩歌出現最多的關鍵詞入手,我暫且昵稱或戲稱為“詞典”。
白晝
白晝在《沉船》前半部是出現頻率很高的一個詞,與此相近的還有太陽、黎明等。它們隐喻着這條大船要駛去的方向和未來。為了黎明降臨,為了讓白晝更長久甚至永恒,船上的人一代代付出了血和命的代價。連我們在閱讀時,心都好像被繩索拽得很緊,像走在懸崖上,小心翼翼,每一腳都要穩準狠。
可見翼人在寫作時是很用力的,生怕輕描淡寫不能表達中它的悲壯和艱難。走向白晝,他們滿含熱淚,但又必須承接苦難,準備犧牲,于是他們用“一顆頭顱還去另一顆頭顱/去追趕一隻受傷的黑鷹”,然而結果卻是“而西風已過/并未露出更本質的白晝”。白晝是頑固的,但比白晝更頑強的是決心和毅力。他們把自己的靈與肉還有期待和希望一點點夯進黑夜,去兌換比金子還珍貴的光明和未來,這是一個民族繁衍生息的理由和氣質。《沉船》就是以這樣近乎殘酷的方式表達了人類追求正義幸福和美好的願望和行為。
黑
和此顔色相關聯的有黑夜、黑狼以及絕望、死亡、葬儀等等。這是和白晝相反的一組詞彙和狀态。它象征人類在追求光明和美好時候遇到的苦難以及必須遭受的彷徨和折磨。這是一種命運。可是經曆了劫難也不一定就能得到幸福。有時候犧牲是無效的。然而犧牲和劫難又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你不要它,它也會不請自來,隻要你在船上,隻要你還活着。
所以人們在經曆了劫難和絕望甚至死亡的考驗之後,對黑暗和犧牲已經習慣,甚至是樂觀:“沿着寒冷的冬天/在注定死亡的陰影下/溫暖上升此刻/風暴襲擊着大片沙漠卻有/一對戀人苦苦地相愛/但當夜幕降臨時/唯獨留下一句話:‘我死就死在你的懷裡’”。這起碼有兩層意思,一黑暗和死亡吓不倒渴望光明的人們;二愛情讓人蔑視死亡并使死亡充滿光輝。這就是翼人對黑暗和死亡的回答。應了那句忘記了誰寫的詩句:即使大雪封住了所有的路/也有向遠方出發的人。
追尋
這是貫穿在這部長詩中最多的一個詞。是前兩個關鍵詞的結果和細化。它可以引申出犧牲、殉道者、英雄。這部長詩确實塑造了一個為了追尋敢于殉道的形象。這形象不是具體的,甚至有點瑣碎和散淡,模糊着卻時時感受到凜然和一往無前的氣勢和氣概。也許就是作者自己的一種英雄情結。但追尋什麼呢?目标并不明顯,也許就是生生不息繁衍下去,并且和平與美好。為了這将要遭遇更嚴酷的考驗甚至犧牲。我眼前隐約浮現蘇格拉底和屈原迎風而立的形象。
為了堅持思想為了求索真理,不怕任何磨難。他們明白美好的活着是需要無數的死來奠基的,這樣死就是最燦爛的美。像德國詩人哲學家西美爾說的:“死亡是最高的生命,必須以死來作獻祭。”這就是讓濃縮的生命達到最純淨的形式。當然它的前提是信仰,為了信仰去死就是不朽的殉道者。所以作者對于這樣的犧牲是豪邁和柔情的:“如果犧牲是一部情書/它将是大家最親密的朋友我的愛人/或在以後的日子裡我們更加相依為命/不管旅途多麼遙遠燃燒的光焰/正在喚起衆多攢動的人群/躍向最深入我的玫瑰花園”。
生命
由此相關的是我和人。不是敢于犧牲就不珍惜生命。生命就是我,就是人,就是尊嚴和世界的中心。對人的了解,對人類的關懷首先是從對生命的關切和尊重開始。但是在過去的歲月裡,有些生命被壓制成一種标本,一種模具,甚至河裡的石頭,河邊的蒿草。所以翼人呐喊:“成千上萬的人要以生命為本/以自由為舞”。他也深情呼喚:“呈現生命的生命呦/你仁慈的愛巨大無比/令我在燭光下一次次懷想你們”。
尊重生命,并讓它自由,給它愛,也讓它自由地愛。這其實就是活着的目的和意義,對于所有生命來說(不僅局限于人),還有比自由和愛更崇高的東西嗎?自由和愛是所有信仰和宗教最終要達到的境地。這才是徹底的解放生命,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可問題是到了現在,人早已經失去了人特有的資質,人變得不是“人”了。這是這部長詩一直掙紮和耿耿于懷的地方。那麼人究竟發生了什麼呢?——
存在
這是這部長詩思索質問的中心。和它關聯的是現在、現狀。這是詩人和哲學家思考的命題。我這裡隻取人的存在和現狀來讨論。如果像上述詞典所言,人是以自由為基本狀态,那麼現在人早己失去了人的特質。人在異化。現代化的副産品是讓人變得程序化,人的行為基本是互相複制。人腦在萎縮,感覺在遲鈍,靈性在逐漸消失。這樣下來,人将不會思考,不會愛。人将不再是人。這樣人類這支大船就真的要沉沒了。這是翼人最擔心的。
所以他在這首長詩裡呼喚人要像人那樣活着。要感覺,要思想,要自我,要愛,要創造。沒有思考的生活就是和豬和機器人一樣。所以人還要認識自己,繼續追問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像哲學家施勒格爾說:“人應該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和自由來進行一場革命,最關緊要的就是人要擠出自己的全力去尋找到自己的中心。人要麼就是毀滅自己,要麼就是自我更新,沒有第三條路。”自我更新就是将人還原為人,讓世界回到最初的那種狀态中去。
時間
這是這部長詩中讓人焦灼的詞彙。它相對應的是有限與無限。生命的有限與時間的無限注定了人的悲劇性。翼人直接寫時間對人和生命的摧殘:“我依然是我豈能畫地為牢/或許時間的結局/令人難以想象/一夜間/飛翔的翅膀鮮血淋漓”,還有“時間如此匆忙地離開我的腦門/滑向目不所及的地方”。
人是多麼脆弱,不僅在存在面前無能為力,在時間面前也是手足無措。那麼怎麼能讓有限的生命變得主動呢?那就是給時間以生命和美,時間盡管無限,但是很多是無用的相當于垃圾,那麼屬于有效的時間就是給時間填進創造還有美和愛。這樣時間就有了内容,從而生命化了。像哲學家謝林說的“當藝術把持住了人的消逝着的流年時,當藝術以完滿健動的美來表現一位已把兒女撫養成人的母親時,藝術難道不是把非本質的東西——時間,給取消了麼?完滿的存在——也隻有一刹那。”這就是瞬間化作永恒。因為有了藝術和意義,一刹那的時間勝過無限。
家園
這是翼人一直在追尋的港灣,也是這艘船離開和要抵達的原因和地方。因為故鄉被打碎,所以要流浪,因為找不到新的家園,船可能就要沉沒。家園是這首詩的開始也是結束。這裡不是給具體生命尋找依靠,而是對“類”,就是部落和民族。“試問何處是我美麗的家園/何處是我肥沃的土地/帶着陣痛和稀有金屬碎裂的夢想/一躍巨人的頭頂/遙想世紀末金黃的麥穗”。
這就是離家漂泊的迷茫和苦澀。那麼方向在哪兒呢?德國詩人生命哲學家荷爾德林晚年把人的最終歸屬定為“返鄉”。他認為最好的家園就是故鄉,是我們出生的地方。人最後的皈依就是“還鄉”。荷爾德林在預感到人的不可逃避的無家可歸之境的同時,也預感到人類必将重返故裡,重返童貞。還鄉就是返回人詩意地栖居的處所,返回與神靈親近的近旁,享受那由于偎伴神靈而激起的無盡的歡樂。這就是詩化的生活,就是詩意的人生(這也是劉小楓對荷爾德林“還鄉”的解釋)。翼人在這部長詩裡也說:“我的回答仍是天人合一”雖然不明确,但是也隐約感覺到要回到當初,擁抱自然,并認為這是最詩意的栖所。
愛
這是這部長詩最清楚的指向。也是翼人認為拯救沉船的藥方。不論是個體的生命還是民族,都應該具有并堅持這種品格。愛是動力,也是人與人、民族與民族、人類與世界之間和諧劑。愛能讓戰争停止,能抹平仇恨,能讓沉船新生:“在過去的歲月裡/我們親如手足”,“歡呼吧我的子民們/是你們拯救了又一個民族的精靈/看到眼前的現實風風火火/正在化為重天的麗日/我的心已得到片刻的甯靜”。
這就是愛的力量。在現代人普遍迷惘,甚至沒有了思考思想還有信仰和方向的時候,愛就是他們的宗教和神話。愛給他們勇氣和熱情,愛讓他們自我更新,讓他們找回自我,重拾靈性。但隻有愛是不夠的。因為愛隻是基礎,是人成為人的最基本的元素,處于人的守勢,屬于溫飽階段。人要發展,還需要有更大的意義和理念來支撐自己,來揭開人生的秘密,來給世界更大的價值。這就是理想或者信仰,就是詩歌中稱之為的神,人需要有一個自己崇尚并為之願意獻身,而且對别人和世界有益的大于自我的神。
神
在這部長詩中,也稱之為夢、理想。它是翼人寫作此詩的動機和推動力。神不論是對翼人還是世界,它都是一種救贖。救贖自己的靈魂,拯救危機的世界。人不能活得太平庸,太自我,太放任,人要給自己的生命設計個意義,這個意義就是人生活下去的中心和根據,這就是人心中的神。
對于翼人來說這個神還是詩,因為詩高于我們的生活,猶如我們仰望的神。他用詩歌來推動鏽迹斑斑的古船,用詩歌去照耀還蒙蔽還黑暗還寒冷的心靈,讓詩鋒利自己的感覺,讓感性變得更敏銳,讓人的心靈變得更偉大,也讓人的胸懷更遼闊和溫暖。這神有時高高在上俯視你;有時又像母親一樣溫暖,像情人一樣柔情。詩人在烤熱自己的同時,也用它去溫暖更多人的心靈。像施勒格爾說的:“詩的任務不在于維護自由的永恒權利,去反抗外部環境的暴虐,而在使人生成為詩,去反抗生活的散文(指平庸和低俗)。追求詩,就是追求自由,詩的國度本身就是自由的國度。”這就是神的光芒和必然,也是翼人寫作此詩的宗旨。
阿爾丁夫-翼人
一個青海高原的漢子,一個用詩歌為民族命名的撒拉爾族詩人。他擁有大的視野大的氣度。所以他對這類大而沉重題材舉重若輕。這種題材很容易寫得大而空,或者撲朔迷離。但翼人的品質讓他把這首大歌唱得結實而低沉,甚至有點憂傷有點沙啞。前半部像唢呐吹出的江河水,在高山峽谷中或蠕動或直沖;後半部像在平原大河中揚帆,昂揚而疾速。中間還有間或的停留和修修補補。可貴的是翼人能從小的細節出發,來表現宏大的題材,這就使詩歌離我們很近,有了可把握性;同時從身邊熟悉的具體的意象入手,表達神聖和神性,就使詩歌有了親切感;而更可貴的是他的表達和抒情都是很溫軟甚至深情的,有時淚花閃爍,這樣的方式表現悲壯,讓悲壯有了溫暖和人間的味道。
《沉船》目錄
CONTENTS
不斷淬煉的精神升階書(代序)
——論阿爾丁夫·翼人的長詩《沉船》……………………………………霍俊明
SpiritualUpgraderontheQuenching(asapreface)
—OnShipwreckedbyAerdingfuYiren…………………………………HuoJunming
沉船(長詩)………………………………………………………………阿爾丁夫·翼人
Shipwrecked(ALongPoem)………………………………………………AerdingfuYiren
《沉船》:人類前行的精神簡史
——解析阿爾丁夫·翼人長詩《沉船》的哲學意義…………………………李犁
Shipwrecked:aBriefSpiritualHistoryofHumanAdvancement
—OnthephilosophicalmeaningofShipwreckedbyAerdingfuYiren……………LiLi
精神尋根的詩性觀照
——讀阿爾丁夫·翼人的長詩《沉船》………………………………………吳投文
PoetryPerspectiveinSpiritualRoot-Seeking
—OnreadingShipwreckedbyAerdingfuYiren……………………………WuTouwen
我譯阿爾丁夫·翼人…………………………………………………………………張智中
AerdingfuYiren,AsITranslateHim…………………………………………ZhangZhi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