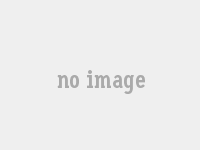人物簡介
田中芳樹(TANAKA YOSHIKI)原名田中美樹(たなかよしき),男,他是日本學習院大學研究院的日本語文博士,但也對中國古代文學有很深入的涉獵。在他的作品裡,很容易看到《三國演義》的影子。他又稱為皆殺的田中、著作多數,完結作少數的代表作家。
田中芳樹的作品題材豐富,在科幻、冒險、懸疑、曆史各領域都有佳作,以壯闊的背景、幻想羅曼史、細密的結構、華麗的筆緻聞名。著名的長篇作品有《銀河英雄傳說》《創龍傳》《亞爾斯蘭戰記》。而在以中國為題材的曆史小說方面,則有《風翔萬裡》《紅塵》《奔流》和《中國武将列傳》。并曾與曆史小說名家陳舜臣合着《中國名将的條件》;并與井上佑美子合着《長江有情》。其他作品方面,有《紅薔薇新娘》、《夢幻都市》、《馬法爾年代紀》、《地球儀的秘密》等作品,短篇集則有《戰争夜想曲》、《流星航道》、《中國幻想》、《半夜旅程》等。
田中芳樹一直深愛中國曆史,因此作品往往帶有濃厚的中國文人氣息,筆下的許多人物,不少也都帶有《三國演義》、《水浒傳》、《史記》裡面英豪枭雄的影子。在讀過《隋唐演義》之後,他更锲而不舍地進行大量的研究與數據搜集,寫出了《風翔萬裡》這本詳述家喻戶曉人物花木蘭事迹的作品,當中描寫之細緻、數據之豐富,委實叫讀者汗顔。這個日本作家,曾經師從中國文化大師,寫過傳世魔幻小說,筆下“殺人”成千上萬,也引來擁趸無數,将其與金庸并列。
人物經曆
1952年10月22日生于熊本縣本渡市。
1972年入讀學習院大學文學部國文科。
并在1984年于學習院大學文學部人文科學研究所(國文學專攻)修畢博士課程。在少年時代酷愛漫畫,小學時因身體不好而曾習劍道。自小酷愛閱讀的他,高中時代便幾乎讀遍了圖書館裡的小說讀物,為撰寫小說奠下了理想的基礎。就讀學習院大學時,田中芳樹開始嘗試創作推理小說并參加比賽。
1975年,發表處女作品《寒泉亭殺人事件》,入選學習院大學第四屆「輔仁會雜志賞」。
1978年,以『李家豐』為筆名投稿,以《在綠色草原上......》奪得日本推理雜志《幻影城》第三屆新人獎。自此田中芳樹便從推理及幻想故事的寫作風格中,慢慢發展出自己獨有的筆觸。
1982年,改筆名為田中芳樹,個人第一套長篇小說《銀河英雄傳說》發表。田中芳樹憑《銀英傳》成為日本文壇無人不曉的名字,并在1988年以壓倒性的人氣獲得「日本星雲獎」,順利登上日本暢銷作家之列。其後《銀英傳》這套二十冊的長篇科幻作品中譯本(日文版原着共十冊)進軍中文圖書世界,亦迅速赢得不少贊譽,台港兩地很快便出現了為數不少的『銀英傳擁護者』,除了在新聞組上充滿着形形色色有關故事、人物的讨論之外,更有不少『忠心』的讀者制作研究《銀英傳》及向其『緻敬』的網頁。這部作品亦先後出現了漫畫、動畫及計算機遊戲等等各個不同的版本,足見《銀英傳》掀起了怎麼樣的一個熱潮。
豐富的曆史知識田中的小說通常被稱為“架空曆史”小說,甚至被劃入科幻小說之列,但實際上田中所描繪的主題永遠是“曆史”──側重于政治和軍事的曆史。田中的作品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真正意義上的“小說”,如《銀河英雄傳說》、《亞爾斯蘭戰記》、《創龍傳》、《夢幻都市》和《紅薔薇新娘》等;另一種是貌似小說的“曆史”,如《風翔萬裡》、《長江落日賦》、《紅塵》、《海嘯》、《奔流》等等。
後者講述了有史可考的“真人真事”,他寫這些書的目的隻是為了“讓讀者能夠以愉快的方式了解曆史和人物而已”。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比如《風翔萬裡》中的花木蘭、《紅塵》中的梁紅玉、《奔流》中的祝英台)
作用隻是帶領讀者走入曆史當中,通過他們的眼睛來觀察曆史,用他們的經曆将一個時期内的曆史事件貫穿起來。在田中的筆下,枯燥的曆史變得有聲有色,仿佛死去的時間又複活了一樣。如果各位看過他的《風翔萬裡》,一定會對他将隋唐時期那段混亂的曆史整理得井井有條的本事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是個日本人呀!)。
他對中國曆史的熟悉程度,實在是另絕大多數中國人望塵莫及。此外,田中還編譯了《隋唐演義》、《嶽飛傳》、《楊家将演義》、《鄭和航海記》等描述中國曆史的着作,田中對書中出場人物的生卒年月都做了詳實的考證,可見他嚴謹的寫作态度和對中國曆史的喜愛。(當然,從《銀河英雄傳說》等書中可以看出他的世界史知識的豐富程度也非同一般。)
冷酷的曆史規律和金庸相比,田中書中的“曆史”的味道更濃一些。金庸所寫的是某一特定時代背景下的傳奇故事,由于最初連載在報紙上,書中充滿戲劇性的情節,推動故事發展的是不斷出現的奇遇和巧合。而田中的小說有整體的構想,本身就像是一部沉重的史書,推動故事發展的是曆史的必然性,加上田中經常以後世曆史學家的口吻使用類似“那一年某人**歲,距某曆史事件的發生還有***年”的句式,使讀者在閱讀的時候仿佛能聽曆史車輪前進時發出的不可抗拒的聲音。
田中筆下故事的發展也遵循着曆史發展的規律,他在貫徹這一點上毫不手軟。他在《銀河英雄傳說》裡為了表現“英雄也會死于感冒或刺殺”的理論不顧讀者的強烈反對殺死了兩個主角萊因哈特和楊威利,這與金庸筆下那些總能逢兇化吉的主人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如果重讀《銀英》,就會發現田中早在“野望篇”的第一章中就曾經提到“世事盛衰無常,再強大的國家也終有滅亡的一天;再偉大的英雄一旦權力在握,日後必定腐化堕落。生命亦然。許多戰場上勉力掙紮圖存的勇士,因一場感冒斷送了性命;在血腥權力鬥争中獲勝的人物,喪命于名不見經傳的暗殺者手上。”這也許正是對萊因哈特和楊威利的命運的暗示吧。
金庸所着力刻畫的是人和人的感情世界,而田中寫作的重點則在于政治、軍事以及宗教等等社會現象,即構成社會的人類的總體,所以他筆下的主人公通常是那些創造曆史的帝王将相們,而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也往往是社會制度發生徹底變革的群雄逐鹿的曆史時期。
比如《亞爾斯蘭戰記》實際上所描繪的就是從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的時期,而《銀河英雄傳說》的故事雖然發生在未來,其社會制度的實質是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階段。從故事的結局我們可以猜測田中的政治觀點偏向于“改良”。他所贊成的是統治階級内部進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比如《銀英》中最終采取的實際上是君主立憲的制度。
尖銳的政治批判田中經常被說成有“政治潔癖”。這也許是因為他對所謂的政治家的腐敗和政治陰謀進行了大膽的揭露。比如《銀英傳》中的特留尼西特等人,使讀者總是不自覺地聯想起現實中的一些人和事,不由得對田中的敏銳洞察力和勇氣佩服得五體投地。
尤其在《創龍傳》中,因為故事發生在現代的日本,田中一改以往的“指桑罵槐”,對當今的日本政府進行了直接的毫不留情的抨擊,他還在後記中号召讀者“趕快去買此書吧,也許過幾天就會被文部省列為禁書了!”不過我個人以為,這樣的書在日本仍能出版,可見日本還是有一定言論自由的。正因為田中常常在嬉笑怒罵之間将政客們陰暗的伎倆輕松地抖露出來,明白得似乎連小學生都能讀得懂似的,所以有人戲稱他的作品為“政治學的小學教材”。
可望而不可及的民主“所謂政治,永遠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但在田中心目中最彌足珍貴的詞大概就是“民主”了。對于“民主”與“專政”的辯論是他作品中的一大主題。最壞的民主和最好的專政究竟哪個更利于人類社會的發展?田中本人傾向于選擇民主,但對這個問題的态度也存在一定矛盾之處。
他的作品中最接近作者本人形象的人物是《銀英傳》中的楊威利。與曆史的創造者萊茵哈特相比,楊是作為曆史的評論者,即作者的代言人出場的。雖然田中在《銀英傳》中描繪了一個腐敗的民主體制和一個在萊茵哈特的領導下近乎完美的專政政體,但正如書中的楊威利所說:“不能因火災而否定火的價值。”而楊本人也為了自己心目中的“民主”而奮戰到了最後一刻。深知民主政體也并不完美,且必将導緻種種社會弊病的産生,田中也沒有将其徹底根治的良策,但他相信至少與“專制”相比,“民主”是人類更好的組織形式。
田中所崇尚的“民主”主要是思想上的自由。雖然寫的是曆史,但他無疑是在“以古喻今”,作品中的很多情節都能在現實中找到原形。與金庸相比,田中筆下的人物更具有現代感,毫無封建思想的束縛。對于那些不擇主君的愚忠的滿嘴儒家道德的臣子們,比如《紅塵》中的李若水,他所有的隻是憐憫。他最蔑視的就是那些懶得用自己的頭腦思考的“思想奴隸”們。
他對廣大麻木不仁的民衆們表現出了強烈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色彩。“讓獨裁者有機可乘的其實是那些不願花精力思考問題的沉默的旁觀者。”“民衆所喜愛的并非自主性的思考及随之産生的責任,而是命令、服從及責任免除。在民主政治中,該為政弊負責的是選擇不合格的從政者的民衆本身;而專制政治則不然,民衆不願自我表現反省,而喜歡輕松且不需負任何責任地大肆抨擊為政者。”
因此,要實現真正的“民主”,首先必須有民衆的覺醒。不可避免的戰争人類的曆史總是與戰争聯系在一起的,朝代的更替更是建立在無數的鮮血與枯骨之上。對于“戰争”,田中也有很多睿智的評論。他曾借楊威利之口說過:“有史以來,人類的思想大體可以分為兩類:有些人認為存在某些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另一些人認為沒有任何東西比生命更可貴。當人們發動戰争的時候,就鼓吹前者;當人們想要停止戰争的時候,就宣揚後者。
于是,戰争與和平就這樣不斷重複下去。”“在人類曆史上原本就沒有永久的和平,所以我也不會有如此的期望。可是,隻要有幾十年的和平就可以使時代富足了。如果我們必須為下一代留下某些遺産的話,我想最好還是和平吧。而把前一代遺留下來的和平維持下去,那就是下一代的責任了。如果每一代都不忘記自己對下一代的責任的話,那麼大概就能保持長時間的和平了吧。如果忘記了這一點而把先人的遺産坐吃山空,那人類就得再從頭開始了,那也不算壞事。”
正義不在成者王侯敗者寇,這是冷酷但客觀的曆史規律,并不存在永恒不變的正義。所以在田中筆下,那些以華麗的詞藻來渲染“正義”的,往往是最不義之人。“我最讨厭的是把自己藏在安全的地方,然後贊美戰争,強調愛國心,把别人推到戰場上去,而自己在後方過着安樂生活的人。”“莫大的流血,國家的破産,國民的窮困。如果要實現正義就不能缺少這些犧牲的話,那麼正義就好像是一個貪欲之神,絲毫不知廉恥地要求一件又一件的祭品。”
與金大俠所說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不同,田中對于“愛國主義”毫無贊美之意。“國家”是什麼?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實行專政的工具,或在戰争中有共同利益的人的集合。所以對于戰争雙方維護自身利益的行為并沒有讴歌的必要。“無論是名将或是愚将,其殺人的記錄是一樣的。愚将殺害了自己一百萬人時,名将則殺了敵人一百萬人。”“兵學所存在的意義就在于以最小的犧牲換取最大的成果。殘酷地說,即是如何有效地殺死自己的同類。”在殘酷的戰争中,隻有生存下來的一方才有資格談論所謂的“正義”吧。
瘋狂宗教也是曆史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與對戰争的态度不同,田中給與宗教的是幾乎完全負面的評價。比如《銀英傳》裡的“地球教”、《創龍傳》中的“神聖真理教”、《亞爾斯蘭戰記》中的依亞爾達波特教和魔道士們,充當的都是不光彩的角色。田中對于宗教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它們所宣揚的對所謂“絕對真理”的盲目崇拜和消極遁世的思想。
在《創龍傳》中田中寫道:“人可以不擇一切手段,隻為了貫徹宗教的信念;當神、國家、民族、思想這些名詞成為一種瘋狂信仰之時,理性與人道觀念頓時灰飛煙滅,轉移成無限的自我正當化,所以他們可以殺害嬰兒、在地鐵散布沙林毒氣、以機關槍掃射非武裝的民衆……”
雖然田中認為“真理”可能是不存在的,但他并不主張逃避現實,比如在《奔流》中,他對南北朝時期梁的一代名君蕭衍晚年信佛表示不屑。《銀英》中他對“地球教”的回歸地球的思想的評語是“地球是人類的搖籃,但人長大了就不能總睡在搖籃裡。”而對于《亞爾斯蘭戰記》中的辛德拉國王那樣将自己難以決定的事推給“神”去裁決的懦弱無能之輩,他更是進行了無情的嘲諷。
此外,廉價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與宗教一樣都是田中痛斥的對象。“做壞事的人很少會擁有‘我在做壞事’的自覺,大多數人都是搬出愛啦、國家啦、教祖啦這一類将自己成正義英雄的理由。”他還曾經在《創龍傳》中提到:要煽動士兵們的作戰情緒,就不能把他們稱作“士兵”,而應改稱“戰士”,因為後一種稱呼讓他們感到自己在為“正義”而戰。他們需要的不是用自己的頭腦思考什麼是所謂的“正義”,而隻是一種虛幻的榮譽感。
愛情曆史上的才子佳人是作家們争相描寫的對象,田中則不同。對于田中筆下的愛情,讀者們有不同的看法。總的來說,田中的作品是相當嚴肅的,絕沒有“戲不夠,愛來湊”的情況發生,書中雖不乏才子佳人,但并無纏綿悱恻的描寫,故事中愛情占的比例相當小(真正偏重“愛情”的主題似乎隻有《銀英》外傳《污名》中的“重要的不是誰愛着我,而是我愛的是誰”而已),而且似乎不如讀者們所期待的那樣浪漫。
甚至有不少人懷疑萊茵哈特和他的王妃希爾德之間是否有真正的愛情,亦或隻存在共同的利害關系。縱觀田中的作品,可以發現他心目中的愛情并非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而是表現為一種相互的信賴。女性對于男性的愛使她們全身心地信任和支持對方。比如《銀英》中希爾德對萊茵哈特、菲列特利加對楊威利,《創龍傳》中的鳥羽茉理對龍堂始等等,她們聰惠能幹,都是“英雄”身邊不可缺少的助手。
幽默當然,作為暢銷書,田中的作品在嚴肅中也不乏幽默。比如《銀英》中楊艦隊成員的毒舌吐槽,《亞爾斯蘭戰記》中那爾薩斯對于繪畫的自我陶醉,而幽默成份最多的作品要數被作者自己稱為“搞笑家庭小說”的《創龍傳》了,書中伶牙俐齒的龍堂家四兄弟的鬥嘴總是讓讀者笑得前仰後合。(看這部書的時候總覺得田中好像是在自娛自樂,四海龍王不需花飛機票錢就代替他本人完成了周遊世界的夢想。)另外田中的作品中還存在一些另讀者忍俊不禁的“田中定律”,比如“戰場上的英雄=情場上的白癡”。看到楊那語無倫次的表白、萊茵哈特向米達麥亞請教怎樣求婚的時候,各位都不禁啞然失笑了吧。
說到“田中式的幽默”,就不得不提起“田中式的語言”。在遣詞排句方面田中芳樹可謂與衆不同。由于他的句子中經常出現又多又長的定語,加上中國的翻譯水平不高,經常讓讀者看得一頭霧水(比如《創龍傳》的開頭處寫道:“托急劇的天氣變化和即使預報再偏差也不會破産的氣象局之福,感覺就好像是在棒球比賽九局後半被打出了再見全壘打”。圈子繞得夠多吧?),于是就有人斥責他的語言過于生硬。
(我強烈建議那些因為看盜版《銀英》而得出“田中寫的句子不通順”的結論的讀者們在看了翻譯質量較好的正版書後再做結論。世界上可能會有語言不流暢的暢銷書作家存在嗎?)我個人以為田中的語言隻是有“特點”,而非有“缺點”,他的文學水平并不遜于金庸。且不論他作品中嚴謹的整體構思和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隻是語言的運用就有其獨到之處。
僅舉一例以證明:當楊威利被刺身亡之後,她的妻子菲列特利加有這樣一段幻想:“……在戰亂已是長達一代以上的過去式的和平年代裡,有一位老人,他曾是威名頗具的軍人,但親眼證實的人很少,也從未有人聽過他吹噓自己的武勳。年輕的家人對他寄予七分敬愛和三分淡然,他就這樣過着靠退休金度日的生活。在日光室中放着一把大搖椅,連吃飯的時候他都坐在那裡讀書,靜靜的就像是椅子的一部分似的,日複一日,時間仿佛靜止了一般……有一天,在外面嬉戲的孫女一不小心将球從日光室的入口丢了近來,球滾到老人腳邊。
以前,老人總會緩緩地彎下腰,撿起球來給她。但這次他卻像沒有聽見孫女的聲音似的,動都不動一下。孫女走上前去,撿起球來,由下方仰望祖父的臉,覺得祖父的表情似乎在說些什麼。“爺爺……”沒有回答,陽光映照在老人入睡低垂的臉上。孫女抱着球,跑到客廳大聲報告:“爸爸!媽媽!爺爺好奇怪呀!”聲音傳得好遠好遠,老人仍然坐在椅子上。永恒的靜谧像海潮一樣,緩緩漫過老人的臉……菲列特利加認為,這種死法才适合楊威利。這景象宛然是在現實中真實發生過的,而不是想象中的情景。”
整段描述沒有出現一個表現悲傷的詞語,但卻将那種欲哭無淚的感情渲染到了極至,使讀者深切地感受到一種刻骨銘心的悲哀。
特色标題最後再說說“田中特色的标題”。獨特的标題也為田中的作品增色不少。《銀英》從“黎明篇”中“永恒的夜”到“落日篇”中“夢的盡頭”,充分營造了“諸神的黃昏”的史詩般的悲劇氣氛;《奔流》中的“建康之花、洛陽之夢”充滿了詩意;《亞爾斯蘭》中的“落日悲歌”和“征馬孤影”使讀者身臨其境地感受到血色殘陽的悲壯;還有《銀英》中獨具匠心相互呼應的“過去、現在、未來”、“混亂、錯亂、惑亂”,“因劍而生”、“因劍而亡”……而像《創龍》中“最後一天的下午”、“最後一天的晚上”這種返璞歸真又不失幽默的标題也并非是一般作家敢于使用的吧。
田中的潔癖比如《銀河英雄傳說》中為了不讓萊因哈特和齊格飛之間完美的友情出現裂痕而在裂痕出現前讓齊格飛為保護萊因哈特而死,從而留下一個完美的回憶。又因為“無法想象萊因哈特年老時候的樣子”而讓他的生命像火焰一樣燃盡,使英年早逝的他在讀者心中永遠是那個“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的黃金獅子。
雖然田中芳樹的書中充滿了曆史的沉重感,但讀他的書時讀者盡可放心,《亞爾斯蘭戰記》中亞爾斯蘭和部下們之間永遠充滿了相互信任,《創龍傳》中的四兄弟遇到危機時總可以潇灑地取得勝利,《銀河英雄傳說》中的楊艦隊一直充滿了“俠氣與醉狂”的大家庭般氣氛,而帶着“天真無辜”的表情的特留尼西特最終也難逃羅嚴塔爾的一槍……而像金庸的《天龍八部》中倒黴的蕭峰不斷被陷害這種讓人讀起來憋氣的情節絕不會在他的書裡出現。
田中芳樹慣于以一個後世曆史學家的口氣進行叙述和評說,在描繪曆史車輪滾滾前進的殘酷現實,對當權者的無能與腐敗進行淋漓盡緻的批判的同時,保留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友情等等在各個時代都被人們所珍視的東西,這也正是他“唯美”的表現。
兩者差别
不過金、田二者也有細微的差别。讀金庸的小說的時候大家都是手不釋卷,一氣呵成吧?雖然田中的小說同樣精彩,閱讀的時候不得不時常停下來思考、消化,不然神經仿佛不能承受曆史的重壓似的。(對于田中的作品而言,“老少皆宜”中的“少”需要有個限度。一個小學生可能會手捧金庸大作讀得津津有味,但他能不能讀懂并欣賞田中的作品就很難說了。
比如《銀英》,出場人物的姓名又多又長,且一開篇的序章就是在某些人眼中看似枯燥無味的史書般的“銀河系史概略”,于是好些人就知難而退了。)雖然田中也重視故事情節,但他無時無刻不在試圖将自己對于曆史的思考融入情節之中,即使在如《創龍傳》等較為輕松的作品中也不例外。田中書中的内容總是為了烘托主題而存在的,沒有為了取悅讀者而精彩的情節。
現實批判
正因為追求完美,田中芳樹才會在作品中對不完美的現實進行猛烈的批判。而且也許正因為追求完美,田中才會不遺餘力的營造一種悲劇氣氛。“殺盡衆人”表現了一種日本美學思想。如日本人喜愛國花櫻花,人們崇尚“如滿櫻一般絢爛的飄落”的死亡方式。櫻花生存的時間短暫,不會等到枯萎而是在櫻滿枝頭時華麗的飄落。日本地震頻發,資源稀少,因此人們對于生命常常有一種這樣态度──年華正燦爛的時候死去,将時間永遠停在最青春、最美麗的瞬間。
不斷死去的角色,如同陣陣的落櫻──他們的人生短暫,但如同彗星般耀眼。因為隻有死去的人才永遠不會衰老,永遠不會犯錯誤,永遠保持完美。而且死亡總能給讀者帶來最強烈的震撼,看過《銀英》的人一定會記得終章“夢的盡頭”中萊茵哈特與安妮羅傑最後的對話:“姐姐,我又做夢了。”“夢還沒有做夠嗎?萊茵哈特。”……雖然此處作者的筆調很平和,讀者的心卻仿佛一下子被抽緊了似的。《銀英》結束時不僅萊和楊兩個主角,羅嚴塔爾、先寇布等人氣頗高的配角也死得七零八落。
《亞爾斯蘭戰記》第一部中田中“屠殺”的業績似乎不及《銀英》,但他在後記裡甚至說說要将第一部中比預先設定多出來的人物在後文中加以“删除”!第二部中人們的命運可想而知。也許用《紅塵》結尾處梁紅玉的一句話來概括田中的想法是再合适不過的了:“活着,就是在看着自己以外的人不斷死去。”
人物設定
無需多言,隻要想象一下如果把田中的作品改編成真人版……那簡直是一場噩夢!像萊茵哈特、亞爾斯蘭、龍堂家四兄弟這樣的角色是絕不可能在地球人中找到合适的演員的。
漫畫風格
正因為田中作品近似于漫畫的風格,他的代表作《銀河英雄傳說》和《亞爾斯蘭戰記》都有漫畫版和動畫版,而由CLAMP配插圖的新做《創龍傳》也被改編成了動畫。著名的插畫大師天野喜孝也曾為《亞爾斯蘭戰記》和《創龍傳》畫過很多經典的插圖。說到由道原かっみ改編的《銀英傳》的漫畫版和後來長達110話的OVA,很多事先看過小說原着的人都不能接受漫畫中的人物形象設定,也許因為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不同的但都近乎完美的萊茵哈特的形象吧。
不過田中本人對道原かっみ的人設倒是持肯定态度。道原かっみ在熟讀《銀英傳》的基礎上将正傳和外傳的内容結合起來繪成漫畫,她的改編還是相當成功的。相比之下,中村地理筆下的漫畫版《亞爾斯蘭戰記》過分拘泥于原着,内容毫無新意,畫技也不夠完美。由神村幸子繪制的動畫版《亞爾斯蘭戰記》就要成功得多。緊湊的劇情,完美的人物形象、宏偉的背景音樂和戰争場面使這部劇場版的《亞爾斯蘭戰記》成為日本動畫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女性角色
田中大神一向擅長描寫人物,無論是萊因哈特的霸氣、楊威利的溫和與矛盾、達龍的勇武、龍堂終的頑皮還是其他無數人物,人物性格塑造的都非常豐滿,讓人感覺有血有肉真實可信而且有趣。不過這個評價隻是對全體男性角色而言。田中作品裡的女性角色,卻要失色很多,遠不如男性角色那麼豐富多彩。我對幾部主要作品進行了簡單的排比,發現田中女性角色基本上可以分做三類:毒舌型,理性型和花瓶類。
人物代表
小早川奈津子和藥師寺涼子
面對這兩位,我們隻有匍匐在地口稱女王陛下萬歲的份。這兩個人雖然就物理形态幾乎屬于不同的物質,但是就精神氣質而言,卻是孿生姐妹一般。連田中在怪奇事件簿的後記裡都感歎說有讀者将涼子稱為“完美版的小早川”。她們兩個人,前者在創龍傳裡剛出場時,還隻是個醜陋的反派大嬸,但随着情節的推進,卻逐漸變成了史上最強的“美女”,無論行動還是語言都誇張到将人類最後的理性防線粉碎一空的程度,一句“哦呵呵呵呵”占盡天下風流。即使是四海龍王見到她也隻有落荒而逃的份,生平隻與銀月王打成了平手(有人推測過,即使是亞爾斯蘭裡的蛇王,也絕非女王陛下的對手)。而她的姐妹藥師寺涼子,雖然就誇張程度與力量比起她姐姐略遜一籌,但是若比起嚣張程度,兩人則是伯仲之間,更何況藥師寺警視還有驚人的美貌做為驕傲的資本,對于橫在面前的敵人和躲在後面的上司毫不留情,犧牲者往往先在精神上被她的毒舌鞭打,再被她的高根鞋刺穿,做她的敵人,總之就是一個字“慘”,小說現已經出版了五部,無論是日本警界還是什麼西洋怪獸東方蠱毒都是一樣的下場。
這兩個人可以說是女性極其極端的例子,即使是習慣于誇張的日本漫畫與動畫,如此嚣張的人物也很少見,秀逗魔導士裡的莉娜、GS美神大作戰裡的美神等等已經算是異色的女性跟她們兩個比較,也不值一提。
次級人物
鳥羽茉莉,法蘭西絲
比起前兩位本不該生存在地球的女王來,這兩位還算是比較平凡的毒舌家。從創龍傳與亞爾斯蘭戰記裡,很容易看出,這兩個人在與别人交談時都有濃厚的毒舌本色。(相對于典型代表來說,是平凡的毒舌本色),鳥羽面對自己的父親,法藍西絲面對奇夫,都有精彩的舌戰對攻,讓人對這兩位小姐精神回路的強韌感歎不已。或許她們都有處于困境的時候,但是言辭上的敗北,卻從未有過。
典型代表
希爾格爾·瑪琳道夫,莉蒂亞
希爾德一出場就是做為具備政治眼光的瑪琳道夫家繼承人而出現的,接下來的一系列活動,她基本就是當做萊因哈特的顧問,所談論的話題也不超越政治軍事方面的探讨。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那一晚的描寫,把這個人物替換成男性,也完全沒會有任何不妥。讀者感覺到的,隻是一個具備了政治頭腦的政治顧問,而不是一個女性。小公主的例子更為極端,她的一舉一動,對褚士朗的言談,都和她的年齡不搭配。這麼小的女孩子居然會如此說話,我們隻能感慨她是個人精,而不是一個女孩子。
來夢、花木蘭
沒什麼好說的,完全沒個性沒能力沒感覺的三無主義巨頭。純粹是做為裝飾品存在的,比起用一句話就可以分辨出身份的提督們,簡直就是白開水,淡而無味。
田中的作品裡,女性角色多是這三類,雖然偶爾有安妮羅潔這樣的傳統溫柔女性角色出現,但是就平均水準而言,卻沒有一個正統的女性角色出現過,這不知道是田中的特色,還是遺憾。(作者對花木蘭沒有起碼的認知和見解,顯然用日本女性傳統概括了所有東方女性特征。)